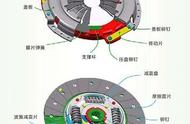青蛙、癞蛤蟆、土田鸡和蛇
春天里,蛙类、蛇类开始从冬眠中醒来,很快进入了繁殖状态。青蛙和蛇的繁殖能力都很惊人,从暮春开始直到到仲夏,田野里到处可以发现他们繁育后代的踪迹。
癞蛤蟆和青蛙是本家兄弟,一个穿得华美光鲜,另一个不太注重衣着打扮,常年都是同一套土灰色并结着疙里疙瘩的外衣。还有一种在旱田和水田里到处蹦哒着的土蛤蟆,潮湿但不汪水的田地里最多。土蛤蟆灰色的衣着打扮和瘌蛤蟆看起来差不多,只不过个子要小得多,多是五厘米以下的小个子,而长大的瘌蛤蟆则有拳头大小。土蛤蟆的皮肤还算光滑,稍微有些小疙瘩,但比癞蛤蟆疙瘩的起伏要小许多。也有的土蛤蟆只是灰色的斑点,几乎看不出有癞子。这种土蛤蟆,我们乡下都叫它们“土田鸡”。而皮肤光滑的青蛙,我们管他们也叫做“蛤蟆”;癞蛤蟆,我们一般就称作“癞癞猴”。另外,在树林里面,草丛和树叶上常有一种碧绿的小青蛙,据说牛吃了会死的。树林里不太深的草丛里,经常有黄绿色相间大大的青蛙,俗称“老黄牛”,应该是牛蛙。放牛时小伙伴们有时会抓住拾掇好烧烤着吃。
癞癞猴和土田鸡在门口就有很多,前院后院,犄角旮旯里,土堆旁,瓦砾下,稻草堆柴禾堆里,蒿草丛里,墙洞中树洞里,到处都是。人走过的路面上,蹦蹦跳跳的癞蛤蟆也不慌不忙地行进着。从门旁的猫洞狗洞里,瘌蛤蟆常常会爬进房屋里,在阴暗的角落里趴在那里,颔下的皮肤因呼吸而像鼓面一样起伏不定。大人们说癞蛤蟆在屋子里面主要吃蚊子和虫子,因此模样恶心的癞蛤蟆,大人和孩子都懒得去搭理它们,任其在屋里屋外自由往来。记得每次雷雨过后,屋前屋后,伏在水坑或者爬来蹦去的癞蛤蟆数不胜数。
青蛙多在水田、河湾、水塘、沟渠、沼泽里面,它们所在的地方,水面相对静止不流或者流动缓慢。深水和激流处,几乎是没有青蛙的。没有水草、浮萍、荷叶遮盖的地方,青蛙也很少见。青蛙是水陆两栖动物,基本都生活在近水的地方。池塘的岸边,小河、沟渠两岸边的草丛里,都栖息着大量的青蛙。走在水田的田埂上,或者漫步在小河、沟渠的岸边,两边不断有青蛙“扑通”“扑通”跳入水中躲避的声音。躲在水中的青蛙,一会儿从水中探出头来,警觉地观察着周边的情况。如果觉得危险解除,它们就会慢慢游回岸边水际线附近,身子还浸泡在水中,腿从水中和岸边接触着,拉出一副随时逃跑的架子。直到确信真的安全了,才会慢慢小心翼翼地爬到岸边草丛里。有时候沿着沟渠岸边放牛时,被牛儿吃草惊起的青蛙和癞癞猴之类特别多。水蛇、赤斑蛇等蛇类也会不断被惊起快速逃逸。
“清明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青蛙的叫声贯穿春、夏、秋三个季节。青蛙从春天产卵时节就开始鸣叫,刚开始夜晚气温还较低的时候,青蛙很少鸣叫,偶尔里“咯咯咕咕”一两声。暮春以后,入夏之初,青蛙的鸣叫就很频繁了,白天叫,晚上也叫。当秧苗都栽种完毕,等秧苗都适应了移栽的环境,开始抽条萌蘖猛长的时期,青蛙的鸣叫愈发密集频繁了。夜晚的点点星空下,十里八里远近不同的水田里面,蛙声从近及远,在由远及近,无边无际,来无影,去无踪,整个夜空就好似茫茫的音乐大海。
青蛙的鸣声在外,最盛于繁星密集的仲夏夜。吃完饭,大人孩子,或坐于打谷场上席地而铺的凉席上,或坐于四条大板凳担成的毛竹凉床上,摇着芭蕉扇,等待一阵阵不时从大坝方向吹来的凉风。大人们拉拉呱,扯扯山海经,张家长李家短,姜子牙诸葛亮,李元霸秦叔宝,张飞关羽,美国苏联的核武器,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有的没的都扯扯。天越热,蛙儿们就鸣叫得越起劲。有时候密密的蛙声几乎不间断地布满在天地间。打谷场四周的癞蛤蟆,也伴随着青蛙们的节奏,莽声莽气地不断应和着。四周的土田鸡也不甘寂寞,用急促清脆的声音加入了蛤蟆家族三重奏。稻田里的点点萤火,地上地下各种不知名的虫子,不待邀请,自愿加入了合唱团。不知为什么,本来只在白天高声叫苦的苦鸽子们,也在不远处池塘蒲草丛里,“苦啊!”“苦啊!”不合时宜地叫着。不知是受不了天气太热,还是对蛤蟆家族的合奏水平表示不满吧。
农民谚语:“夏天蛤蟆叫,大雨就来到。”清晨或午后,房前屋后的癞蛤蟆们,如果突然卖力地叫着,多半是应了上面的谚语。大雨多来自清晨或者午后,特别是湿热的午后,如果癞蛤蟆拼命地叫着,突然沉寂了很长时间,则过不了多久,倾盆大雨就来临了。雨水打起干燥的泥土,空气里满是泥土的芬芳。雨声间歇后,大河小河、池塘湖泊都涨满了水,沟渠河道,门口地面远处秧田里都是流水,青蛙和癞蛤蟆、土田鸡们都一起合奏出最欢快的乐曲,正式宣告由它们主宰宇宙的时刻到来了。
大生产队时,几乎没有人吃青蛙,偶有抓青蛙的,主要是养鸭子的社员,把青蛙煮熟用来喂小鸭仔。大生产队自己也放养着一大批鸭子,不可能有人去抓青蛙喂养它们,鸭子们主要放养在秧田和湖泊、沟渠里面,完全凭自己本事找食吃。极少数社员家里散养着很少的鸭子,幼儿期有一段时间会吃到一些青蛙,稍微长大后可以外出放养后,都是靠在外觅食养活自己。包产到户后,突然间捉青蛙的人多了起来,说是可以卖钱,并且有从城市返回的人,尝试抓青蛙做菜吃。
对金钱和食物的*,诱惑有些孩子去抓青蛙。青蛙在人类面前真的很笨拙,人们有太多的方法可以抓到它们。用竹捎剪一个极小段,栓上细线,做成钓钩,再随便挂个小小的柳树叶,在青蛙眼前故意慢慢晃动,引诱青蛙扑食树叶,就可以很轻松地抓住大青蛙;或者用把子长长的抄网,一下子就能网住最能跳跃的青蛙;甚至将青蛙赶到浅水里,赤脚下去用手摸就可以捉住青蛙。然而更多时候是用叉子去叉青蛙。把粗细适中的铁丝两端磨得尖尖的,拿老虎钳从中间弯成U型,用绳子绑紧在长竹竿的一端,这样的叉子叉大鱼都没有问题,更何况是小小的青蛙了。拿着叉子,循声找到青蛙,看准了,一叉下去就是一个。由于竹竿既长又重,一般的小孩是没有力气的。只有半大不小的孩子才能将叉子运用自如。我的哥哥们都是叉青蛙的高手。我家里每年都散养十几只鸭子,鸭子很小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提着篓子,跟着哥哥出去叉青蛙,几乎每次都能收获半篓子青蛙,用来给小鸭子们改善伙食。一般回家把青蛙煮熟后,再将青蛙肉伴在糠麸青菜为主的鸭食里面,用来喂鸭子。记得有几次,家里人把青蛙除去内脏洗净后,用刀切一切,加点作料,下油锅炒。第一次吃辣椒炒青蛙肉,当时觉得很好吃,似鸡肉一般滋味。但我一听说是青蛙肉后,就特别恶心。虽然抓过很多青蛙,并不害怕这种动物,但真的一点都没想到要去吃它们的肉,而且我是真的不喜欢吃它的肉,就是觉得恶心想呕吐。十里八乡的村里,极少听说谁家经常吃青蛙肉的,那会被人们笑话的,毕竟极为贫穷饥饿的年代,人们没有食物吃,才会去吃青蛙肉。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虽然温饱还没有解决,经常饿肚子,但已经过了会饿死的年代,所以村民普遍厌恶青蛙肉,我也对青蛙肉非常抵触。就连小学课本中都告诉我们,青蛙是益虫,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应该保护吃害虫的青蛙。青蛙的手掌,仔细观察,犹如我们人类的手掌,吃青蛙肉,心理实在难以过关。
后来生活好了,刚到城里生活时,菜市场里面也有个别人挎着篮子,偷偷摸摸地卖青蛙腿。有些人觉得青蛙腿肉真的很鲜美,但我依然如故排斥吃蛙肉,即使在饭店里吃昂贵的牛蛙肉,我也是从来不愿意去动上一筷子的。直到现在,饭店里的牛蛙肉,不管谁说再怎么好吃,我也绝不会伸出筷子碰一下的。这和我现在不愿意吃腌菜的情形,是完全不相同的原因。
好在家里就炒过几次青蛙肉,大多数家人都觉得恶心,后来就没有人再去炒青蛙肉吃了。我们抓的青蛙主要作为小鸭子们的点心。那时候村里放鸭子的就两家,我们家放了十几只鸭,腊月*了做板鸭,用来弥补过年时肉食不足的缺憾。那时的鸭子没有圈养的,主要是放养。早晨赶到河里或者湖里、田里,任其自由吃螺蛳或者鱼虾,晚上再赶回家。期间放鸭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严防鸭子进入生产队有粮食的田里,因为糟蹋粮食会被队里扣留并罚工分。如果是在没有抽穗的秧田,或者作物还有开花结食的旱地里,鸭子吃些害虫,生产队则欢迎鸭子们下田灭虫。
小鸭子的饲养的的过程中,要想长大,就必须及时补充营养。因为开始的幼鸭太小,不能靠天天打青蛙喂鸭子,太麻烦了。青蛙也不能抓太多了,那样会被村里大小的管事的训斥责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青蛙能吃稻田里面的害虫。生产队的时候,稻田里面几乎不打农药,打农药的习惯是在包产到户以后才逐渐增多的。也是包产到户以后,打青蛙、抓蛇的事情逐渐多了起来,因为镇上有人收购青蛙和活水蛇,据说要卖到很远的地方。再后来,不知是农药打多了还是人们私下抓多了,青蛙和水蛇都越来越少了。派出所后来加大了打击力度,贩卖和收购青蛙、蛇都被严格禁止,捕*青蛙和水蛇达到一定数量时,还会被拘留、罚款。后来也没有人再去抓青蛙和蛇了,但显然它们已经不太多了。农村现在盛夏夜晚的蛙声,和我小时候的蛙声比起来,声势犹如天壤之别。
因为不能天天抓青蛙喂鸭子,鸭子在换毛之前,需大量吃荤才能迅速成长。夏天正午时分,大哥会挑着粪桶,拿着长把粪舀子和长柄细滤网,到处找别人家的粪坑,过滤在粪水里爬来钻去、起起伏伏的蛆虫,放到粪桶里挑回家。再到一段废弃的沟渠里,将蛆虫冲洗后放入水中,蛆虫们漂在水面上不断蠕动着白白的身子,鸭子们在水里划着水,欢快地吞食着蛆虫。吃了蛆虫的鸭子,因为营养太好,很快就会长出四点毛来。
秋天稻子收割后的田里,有收割时遗落的稻粒,有乱蹦的青蛙和各种蚱蜢、螺蛳。在生产队拾穗的人捡拾过后,这时候可将鸭子赶进稻茬田,鸭子们东追西跑,很快就会嗉囔饱胀,吃饱喝足。傍晚回家时,鸭子们都会缓缓地迈着脚步,志得意满,不时发出“嘎”“嘎”的低叫声。
有一年我家的鸭子,因为父亲生病,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去管它。从秋天开始就漂泊在老藕湖里面,深秋季节一直到湖面结冰时,都和一群野鸭、大雁、天鹅们混在一起。到深冬季节,野鸭、大雁、天鹅们都飞到南方过冬了,而我家的十几只鸭子却漂泊在湖面,过起了流浪鸭的生活。我们在岸边怎么吆喝和拿竹竿赶,都赶不上岸来,面对茫茫湖面,束手无策。岸边的田里,靠岸的湖水里,经常有人捡到鸭蛋。这些鸭子,直到过年也没有能被赶上岸,这年过年时,第一次没有吃到家里卤制的板鸭。第二年夏天,湖里有人用船放置粘网捕鱼,鸭子被他们惊上了岸,才被大哥赶回家关了起来。泛水于五湖,逍遥快活了近一年的鸭子们,终究没能躲过命运的劫数。
至于村前地头随处可见的癞蛤蟆,平时大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一下雨就房前屋后乱蹦乱跳的。我一看到癞蛤蟆那一身的癞疙瘩,心里就起腻歪。不过,还有更意外的事情让我震惊:我竟然见到有人吃癞蛤蟆!小时候,邻居家大牛头上长了一头疮,好长时间,抹些膏药,还是不见好转。大牛的妈妈按辈分,我们该叫她二奶奶,但她太年轻,两个儿子和我们差不多大,所以对她大儿子大牛,有时就乱叫为大牛哥,其实应该是舅舅辈分的。小儿子小老军比我还小,天天在一起玩。我们村里孩子的小名前都加一个“老”字,前面再加一个“小”字。像小老军、小老四、小老群等等。不在正式场合里,我们孩子间私下里经常不按辈分叫的,好在他们兄弟俩也没有什么长辈的架子,总是和我们小辈们打成一片,有时候甚至还会被我们欺负后委屈得哭鼻子。
有一天,二奶奶神秘地对小儿子小老军说:“小老军啊!你去抓几只癞癞猴来!”结果小老军就叫上我们几个,陪他一起去。听说癞蛤蟆会喷毒水,沾到皮肤上,皮肤就会烂掉。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几个,有的拿上火钳,有的拿把锹或铲子,再带个破篓子,穿过好几家的庭院,来到大老刘家破败的院墙边。从碎砖瓦片围成的空洞里,抓了几只癞蛤蟆。在这期间有过数次,透过砖瓦的缝隙,我们看到墙角洞里有蛇花花绿绿的身影出现。我特别怕毒蛇,小老军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非要翻砖倒瓦地把蛇们捉住打死。大老刘是个乐呵呵的中年人,有一年得一种不知名的怪病,直着脖子嚎叫了好几天,突然就死了。他漂亮的老婆没几天就跟人跑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也一起带走了。大老刘是外来户,三十多岁时,才娶了个外地逃荒来的年轻姑娘。他没有亲戚朋友在此,他死后,村里人都说他家宅子不吉利,屋子也就没有人愿意再去住。大老刘家的院墙倒塌好多年了,房顶上都是各种旺盛的野草和蒿子。院子里的蒿草荆棘都有一人多深。据大人们闲聊时说,大老刘不是好死的,因此空旷的院落里,在月黑风高之夜,常常有人听见大老刘深深的叹息和痛苦的*声。我们既怕被蛇咬着,也怕招惹了大老刘的阴魂,硬是劝小老军赶紧回去交差。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我们几个人赶紧拿着工具,带着几只癞蛤蟆,急匆匆地离开了。路上不断埋怨小老军为什么将我们带到这恐怖院落来。
大牛的妈妈将癞蛤蟆剥皮抽筋,除去内脏后洗净,加水煮熟,再加点作料和油盐,二奶奶把我们赶出去,偷偷摸摸地端给大牛吃。我们几个透过窗户,看到大牛吃得那个贼模样,我们惊讶得合不拢嘴。小孩子毕竟对什么新鲜物事都好奇,我们一边担心大牛会不会死,一边议论起这个癞蛤蟆究竟啥滋味。小老军偷偷溜进厢屋,用碗盛了一点,端到外面草堆头边,让我们几个一起尝一下。你推我挡僵持了一会儿后,有人尝了一点,我也尝了一下,恶心地赶快吐掉,他们几个也一样,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美味。想到癞蛤蟆的样子,作为食物,有人如果不觉得恶心那肯定不是人类。
以后我们还帮小老军捉过几次癞蛤蟆,不过不知为啥,到了秋天,大牛一头癞子样头疮真的不见了,皮肤除了非常黝黑之外,一切都平复如初。
在乡下,青蛙癞蛤蟆多的地方蛇也多。
青蛙和癞蛤蟆,都是蛇的好食物。我见过很多次蛇缠青蛙或者癞蛤蟆的场景。有时候还把蛇打跑,去解救它们。
村里村外的蛇的数量极多,有毒的无毒的都有。水蛇和一些无毒家蛇类随处可见,田头垄边,毒蛇的身影也是不难发现的。有时候家里也会有护家吃老鼠的蛇类出没,甚至厕所边都会见到抓老鼠的家蛇。家蛇无毒,家蛇进了家,不能去打,更不能去赶,赶走它们就把家里的旺气赶走了,以后想发财都困难。小时候曾用手去拽墙洞里蛇的尾巴,有些嫩黄色发绿的家蛇使劲往老鼠洞里面钻,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得手。偶尔抓出来,在大人的呵斥下,也是放手任其钻进鼠洞或者角落里面。
毒蛇进了院子的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毒蛇进家的情况,我亲眼见过一次,刚好在村头大奶奶家。好在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什么事故。其它的无毒蛇或者有毒蛇,在村头路边时有出没。出现在院子里的蛇,一般在屋前猪圈附近,或者靠近厢屋的角落,最多的是在后园菜地的沟渠、池塘不远的旱地上。我们乡下的毒蛇多是土公蛇和赤斑蛇。
这两种蛇,极少在院子里出没。但在村子里荒草荆棘丛或者废弃的院落和园子里面可以见到。
作为无毒蛇的水蛇,除了女子会天然怕蛇外,村里的半大男孩子都不会畏惧它们。用手去抓水蛇,除了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外,别的到没有什么。即使被水蛇咬上一口,也不是特别疼,不过手上略有痕迹罢了。抓水蛇不是为了吃蛇肉,水蛇肉味道一点也不好吃。村里人除非荒年饿极了,没有人主动去抓蛇吃肉的。只要有食物吃,我们乡下没有任何人愿意吃蛇肉。我想这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原因,朴实的农民们也觉得蛇吃老鼠,可以保护住庄稼。
包产到户后,有一段时间,集镇上有人在墙上写上“大量收购活水蛇”的字后,乡下抓水蛇卖的人多了起来。我们在四月底五月里,光着脚,带着纱布手套,拿着火钳,拎着蛇皮袋,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到麦田和油菜田,或者荒滩,河坎处寻找水蛇,抓起来卖。这时候的蛇都是一窝一窝的,非常好抓,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有手抓起来。带火钳子主要防止毒蛇,毒蛇没有人抓,收蛇的也不要毒蛇。有一次我光着脚,差点踩到一条土公蛇;还有一次,看见田埂上一个洞里有花花的蛇,竟然伸手去探,幸亏洞太深了没有触到。后来用钳子使劲夹出来,结果竟然是土公蛇!当时就扔了钳子。现在想来,这几次真是很幸运的事情。
水蛇被抓住后,都卖给了收蛇人。开始几毛钱一斤,后来蛇少了的时候,能卖到一元多钱一斤。再后来,蛇和青蛙类都不准买卖,抓蛇的人就绝迹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蛇被抓的太多了,还是农药的大量使用,乡下本来随处可见的水蛇,竟然也很少出现了,即使国家的保护措施越来越严厉。
据说抓蛇主要是需要蛇皮,我一直认为蛇皮袋也是蛇皮做的。有一次,我问小老三:“剥蛇皮是为了做蛇皮袋么?”小老三思考了半天,肯定地回答我“当然是啦!要不怎么叫蛇皮袋呢?”
水蛇一般都不大,模样长得像黄鳝,只是皮粗糙难看颜色不同罢了。我讨厌蛇,连带长的相近的黄鳝也被我一起厌恶起来。除非真没有什么吃的,否则我对黄鳝肉也是拒而远之的。
我见过有人吃毒蛇肉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谁吃水蛇肉的。毒蛇可以长得很肥大,肉比水蛇多许多,据说熬汤后有老母鸡汤的味道。有一次晚上,旁边邻居大哥在草堆旁打死一只肥大的蝮蛇,剥了蛇皮,肉看起来肥嘟嘟的。斩去蛇头,破开蛇肚,掏尽内脏,清洗干净,加点作料,熬了一锅汤。雪白的蛇肉,雪白的浓汤,闻起来有一股香味,看起来很鲜美的样子。
赤斑蛇,也就是赤练蛇,晚上去水田粘泥鳅和黄鳝时,经常能在经过的荒滩、树丛里看见。赤斑蛇很少在水田里面出没。不过经常见到大孩子们打死赤斑蛇的场景,但没有看见和听见谁将其变成食物的,多是拿起来捏着尾巴,甩成一个圆,突然松手,长蛇划着抛物线飞向远处。落地后,有人跑过去再捡起来拿着,如法炮制,直到所有人都失去兴趣离去。蛇的尸体就随意弃在路旁。因为听说其全身都是毒,没有人敢去尝试,想来只有五九年会有不怕死的人才去吃。我们这地区蛇的种类不是太多,除了以上容易见到的蛇类外,河埂上杂树林中常有长长的锦蛇出没,锦蛇没有毒,但长长粗粗的很是吓人。
我曾经在夏夜听大人们聊天时,说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在槐花开的时节,某村有个人夜晚出去偷打槐花,结果被蛇缠死了。这槐花不是洋槐树的花,洋槐树的花可以作为食物,这种槐树的花晒干了当中药卖。这发生在很远处,在两个水库间的一个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开阔地,有一条大河穿行其间,河埂和开阔地里都种满了各种刺槐和豆槐树。这个人就在夜里偷偷摸到那片槐树林里,打豆槐的花卖钱。第二天有个赶早的路人,经过槐树林,在树林里发现打槐花的人,脖子上缠着一条大蛇,靠在一棵刺槐树上,舌头伸得老长,早已气绝身亡。说故事的人最后说:“当路人喊来很多村民时,大蛇还在紧紧缠着,一点都不肯放松,好似打槐花的人前世作了什么孽一样!”最后村民们用长竹竿去驱赶大蛇,大蛇才不情愿地放开打槐花者,快速地消失在树林间。自从听过这个故事后,从此往后,我每次在野外河边行走时,心里都会发毛,除了对河埂边的坟茔有莫名的怯意外,还时时害怕不知从哪里会窜出条大蛇来。因此对河埂荒树林和高高的蒿草茅草丛也连带害怕起来,一个人再也不敢去那里放牛了,虽然河埂边牛可吃的草真是多。
就是对穿村而过的东塘和大沟,我们有时多少也有点敬畏。特别是东塘,中间有个半亩左右的小岛,本来是当初挖塘时泥土不好运走,生产队长就将泥土堆积在塘中央,从而成为一个小岛。起初上面还种了些许豆子、高粱之类庄稼,也种了很多杂树,颇有些槐树在内。岛上土不肥,庄稼长得不好,也没有什么收成,慢慢就没有人去伺候这些庄稼了,岛上只落得荒草萋萋,杂树都东西歪斜,土里各种洞口纵横交错,很像黄鼠狼或者蛇鼠的洞。我们在塘里游泳时,在岛边确实看到过不少蛇类。最可怕的是有个叫大毛的大人,亲口告诉左邻右舍:他有天中午在塘边汪牛,看见一条长着金色鸡冠的大蛇,从岛上滑进水里,在水里游了半天,大约也是为了纳凉。最后大蛇又游回了岛上。村中有个亲家在皖南的人,告诉大家应该确有其事,这蛇叫鸡冠蛇,皖南山里就有。他亲家公曾经亲口谈起:鸡冠蛇通体金色,头上鸡冠是肉红色的,并且说这是世界上最毒的鸡冠蛇,“对着人哈口气,人就会立刻死去,是万万靠近不得的!”大家闻听之后无不觉得毛骨悚然,我和小伙伴们好长时间里,都不敢在东塘里汪牛了,更别提在塘里游泳嬉戏了。不过此后好多年,都没有人见过鸡冠蛇,慢慢地,大家的害怕之心就谈了许多。在东塘里的活动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只是还没有人敢逾越雷池,登到岛上去的,而岛上的树木和杂草更见荒芜了。曾经有一个夏天,不知从哪里飞来几只大鸟,脚长长的,经常收起一只脚立在水边,歪着头,盯着水里的游鱼,一直能等待好长时间。我们孩子都称它们叫“老等”。这几只老等,曾经占据岛上一段时间,用树枝做窝生蛋。不过不知何故,始终没有见到“小等”的出生。后来不知哪一天,老等都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即使这样,大家在一起闲谈时,话语间还是对岛上的鸡冠蛇颇有敬畏的。
乡下的豆田等旱田里,偶尔会有刺猬出没,邻居家狗子曾经抓过一只,养在家里,夜里还会咳嗽,冬天会冬眠。我们去逗着它玩,非常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