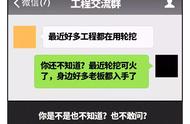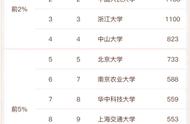原题
知青生活回忆:那时的爱情
作者:王立平
01
那时的爱情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连里来了一批退伍的复员兵,分到各班排当班排长,老何就是那时来的。那时老何也就二十五六岁,四川万县人(现在叫万州),中等个,挺结实也挺能干。四川人都挺能干,这我有体会。老何来后担任一个知青排的排长,老慢就在那个排。
老慢是哈尔滨来的女知青,我家领导施老师的同学。老慢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进城,所以上学晚,因此比施老师大好几岁。老慢是个慢性子,什么事都不着急,慢慢腾腾的。没话儿,蔫蔫的,由此得了一个外号老慢。
文革年代是一个禁欲的年代,人性受到了几乎从未有过的压抑。看看今天的纵欲,也许恰恰是那个年代的反弹。
在那个禁欲的年代,男女之间只有也只能有“革命友谊”,其它的都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女知青是一个“高压线”,知青之间还可原谅,如果是别人动了女知青,那就好比今天的“军婚”,谁动谁倒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部确确实实有极少数现役军人因此而被重判。
前些年,我曾委托一个中介帮我办理买房公积金的手续。那个开车的司机兼业务也是兵团回来的,一聊起来,他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那个连队居然是管理兵团监狱的,里面的犯人有相当部分就是动了女知青的现役军人。不过据他说后来那些军人很多都被原部队接走了,大概军队认为有些人的处理过重。
我们连的这批转业兵中有一个曹姓排长,在连里挺“牛”,见人带搭不理的,谁也不服。说是这曹姓排长有两刷子,不然为何如此盛气凌人。不过我到没看出来他有何德何能,也许是还没有给他……用现在时髦话说,一个合适的施展平台。
大康就不屑曹排长:他有啥牛的?那是他没碰上事儿,碰上了一样啥也不是!
有一次夜班破木头(用电锯把原木破成板子),大康和曹排长在下锯,另一老职工老姜上锯。原木经过电锯推过来,大康和曹排长分别把破开的两部分木头接过来,老曹接薄板子,大康接原木。破木头是个危险活儿,绝不能分神。这老曹心思不知在哪儿转,漫不经心、带接不接的没抓住。那板子被电锯带着“嗖”的一下就飞回去了,直接击中对面老姜胸口,老姜哼都没哼就倒下了。这下老曹急了,架子也不摆了,扑过去晃着老职工:老姜、老姜……
大康定了定神:老曹,我去叫卫生员吧?老曹面无人色,调都变了:你…快…去……
这曹排长就动了一个北京女知青,虽然他不是现役也被重重地处理了,先是将他和那女知青分别调出连队,从此我们就再没见过那女知青,后来曹排长被判刑。
说实话,虽然那曹姓排长是有家室的人,但这事现在看来多少也是事出有因,风传两人心甘情愿,而且据说女知青毫不反悔。
再说老何。
这老何排长不光是能干,心机也不错。一边带着我等知青战天斗地,明修栈道,一边悄无声息地摸了个女知青,暗渡陈仓。一切做得天衣无缝,等到老慢因妊娠反应原形毕露时连里的领导才如梦方醒。估计这时的老何正躲在暗处带着四川农民的狡猾悄悄的笑呢。
老何碰了高压线。
据说连里和上面的人找老何谈话,说的那是既痛心疾首又声色俱厉。你老何怎么就不能多想一想,忍一忍……说来说去把老何说急了:到那关头我能忍得住吗!这句话后来成了我连的一句经典回忆语录。
老何能不急吗?那边老慢刚刚*,大人、胎儿急需悉心照料。这边上级是隔离审查,毫不通融,连面也不让见。至于说俩人急需一间遮风避雨的小屋那更是想也别想。
老何是“怒发冲冠为红颜”!
我老何也是个近三十的大龄未婚青年,况且两人是真心相爱、无怨无悔,不过是“提前点火”、“先斩后奏”,你又能奈我如何?老子来连队几年也是上执行领导指示、下关照连队弟兄,风里来、雨里去,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事儿出了,你领导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老何的四川锤子精神上来了。
话是那么说,可毕竟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那些日子成了老何和老慢最痛苦的记忆。
做为女人的老慢最难受,平日的知青姐妹们疏远她了,主要是不理解她。强烈的*反应,爱人近在咫尺却又如远隔天涯,这一切让她痛苦不堪。没什么好吃的,为了孩子,捡两块砖头在门口“搭”一个简易“炉灶”,自己煮点东西吃。
我家的领导施老师那时和老慢一个班。咱家领导哪都好,就是“觉悟”差,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不管别人怎么说,只以强弱论高低,只要是弱势就同情。现在回想起来,施老师还能说出老慢那时的凄惨样子:整天一言不发,“萎缩”在宿舍大通铺的墙角,瘦得脱了相。施老师常去帮她打饭,问她想吃些啥,想让她多吃点,告诉她:别管人家说什么,保命要紧。别怕,谁欺负你也不行!
精神、生理的双重压迫,老慢的孩子夭折了。那是个双胞胎,两条人命呀!现在当年连里的知青说起那双胞胎还“咂咂”的惋惜。
上级最终也没有把老何和老慢怎么样。
你又能怎么样?当时也是下乡年代的中期了,知青年龄越来越大,实际问题已经摆在了当权者面前。你们他妈的每天回家知道搂着老婆睡觉,我搞个对象你还看贼似地盯着我,你想干什么?老子还想跟你要回我双胞胎的命呢!
老何和老慢正式结婚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
大批知青返城时老慢没有回,她默默地注视着往日的姐妹一个个离她而去。咬咬牙和老何燕子衔泥样的构筑他们的小巢,继续着他们逐渐孤寂的生活。
老何和老慢的苦心没有白费,两个孩子现在都已成人。老大在哈尔滨做买卖,老二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一个著名的酒厂工作。老二把两位老人接到了自己那里。两个孩子都搞得不错,只要俩位老人想出去走走,一定出资出力,大力支持。
我们再一次见到老何和老慢是在2008年。老两口带着小孙子回四川万县老家,回来时路过北京。
两人都已老了,老何圆溜溜的脑袋留着很短的头发(就是那种四川人的圆脑袋,我发现四川男人那种圆溜溜的脑袋特多),笑呵呵的,早已不是当年“怒发冲冠为红颜”的样子了,变成了个慈祥的爷爷。老慢话也特多,长期艰苦的生活不但刀切斧刻般改变了她的容貌,也改变了她的性格。
好人好报,老何和老慢终于熬过来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2
天上的女儿
据说团部附近有座山,叫元宝山。我没去过,我们大多数人都没去过。我们的赵丽华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春风秋雨,已经默默地度过了数十年。
每年我们这些人都会聚几次。说起当年的人和事,常常会提起赵丽华,醉眼朦胧中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赵丽华是我们连的会计,1969年下乡,哈尔滨铁中知青。现在回忆起来都说她是个美女,高个,白皮肤,大大的杏眼清澈如水,椭圆脸上浅浅透着少女特有的红润,两条辫子随着她的脚步在身后微微晃动。
印象中赵丽华常常穿件浅灰色的制服,干干净净、板板正正,连风纪扣都扣得整整齐齐。虽然同一个连队,但她在连部,我在农业排,基本没和她说过话。只觉得她明眸皓齿,迎面而过让你感到似一股清风徐徐而来。不似灿烂阳光般的热情奔放,不似星光月色样的清凉委婉,而是欲露未露的霞光下静静的清晨。
她人很安静,话不多,说起来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给人的印象很好。怪不得连里选她做会计,让人放心。
赵丽华的知青生活只有短短的一年多。
事情发生的很突然,是在冬天。那天她去团部对账,回来搭一辆装满粮食的卡车。车上还有好几个同连队的人,其中一个是个排长,天津知青,姓李。那时搭车是常有的事,马车、拖拉机、当然最好的是汽车。连队距团部几十里,没车就走路,有车尽量搭。他们就坐在高高的麻袋堆上。
离连队只有几公里时,车翻了。人摔了下来,麻袋也尽数滚了下来,小山一样的麻袋砸在他们身上。赵丽华当时就不行了,严重内伤。
其他轻伤的人赶快把她从麻袋堆中拖出来,再跑回来叫人。等把她送到团部医院时,人已经没救了。
那天连里去了几十个精壮知青准备输血。
天阴沉沉的,整个连队一片肃穆。
那个排长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硬汉子。谁也不知道他是重伤,事故现场他一直在组织救人,到团部后又安排其他轻伤员救治,直至昏倒。马上检查,脾脏破裂,腹腔内大量积血,紧急手术摘除脾脏。听说他返城回天津后于前些年去世,应该也就50岁左右,中年辞世我感觉还是和那次重伤有关。
据说赵丽华弥留之际断续*中发出的声音是:账…账……
那样的年代,一句豪言壮语是对逝者的托举,对生者的安慰。不用证实,也无需证实。即使她无言而去,曾经努力工作了,她就对得起一切。献出了生命,她更对得起一切。
赵丽华是连里第一个离我们而去的知青。
她的父母静静地来了,把他们的女儿永远留在了那里。又静静地走了,带走了他们永远的心痛。
赵丽华,这个春天一样的姑娘,就这样以她含苞欲放的十八岁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今天,我们的儿女早已度过了十八岁,甚至儿女的孩子已经出生。
我们回到了故乡的城市,我们喜怒哀乐,我们恋爱、结婚,我们享受着合家欢颜的天伦。
可曾想到,北方的哈尔滨会有一对耄耋老人,婆娑泪眼空对一付碗筷。
他们天上的女儿,他们永远十八岁的如花女儿。
03
施老师
在我们连,有一道至少是男生百看不厌的风景线——收工的队伍。
虽然对风水一窍不通,但感觉我们连的风水应该不错。连队坐落在一个山坳里,三面环山,西面一望平原,连里主要的耕地都在西面。我们住的大宿舍在村子的西头,大部分男知青都住在这个大宿舍里。于是,当收工的人流沿那条所谓的战备公路从西面大地里走来时,在宿舍里的小伙子们就可以隔窗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看女知青了。
在这道百看不厌的风景线里有一个经典镜头,那就是永远走在前面的两个女知青——我将来的领导施老师和另一个杭州女知青凤鸣。
那时的劳作是辛苦之极的,你想想,在地里割一天大豆那是什么滋味。割到后来腰弯下去都直不起来,晚上睡觉一闭眼,眼前就是一垄垄大豆。收工时人已是筋疲力尽,回来的队伍拖的极长。但是不管多苦多累,收工打头走来的一定是她俩。只见两人身体前倾,目不斜视,表情严肃,疾步如飞,最有意思的是俩人个子都不高。
我曾经问过施老师:那时你不觉得累吗?她说下工了心里就只想着往回赶,抓紧打水洗刷干净,然后把自己的小窝整理好,包括把窝里其他人的水也打好,她的小窝包括凤鸣等其他几人。有时她洗刷完毕甚至把衣服都洗好了别人才走回来。
这等醉心于自己小窝的人将来一定是热衷于居家过日子的人。果不其然,现在施老师和凤鸣都是家里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下班就往家跑的人。
施老师是哈尔滨知青,一米六还差点的个子,那时的她是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外号“小不点”。

1969年刚下乡时的施老师
其实她刚下乡时不胖,但很快就像气吹似地胖了起来。咱得说句公道话,兵团苦是苦,但有一点,吃得饱。菜不好,可白面馒头随便。越累吃得越多,回家探亲时一过磅,居然长了20多斤。她爸妈正能量满满地说:还是上山下乡锻炼人啊!后来她回哈尔滨上学,她爸又说:好好学啊,学好了本领再回去建设北大荒。气得施老师说:你是我亲爹吗!
因为她嘴快,叽叽喳喳地不饶人,也不怕得罪人。人又小,没长开,前额圆圆的,男知青又偷偷给她起了个外号小锛头。
成家以后有好几次施老师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摸着前额疑惑地问我:我这儿像个锛头吗?
每次我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咱连男生给几乎每一个女知青都起了个外号,你不叫小锛头也得叫别的什么。
记得我上学刚到石油学校,食堂有个女炊事员,那姑娘腿稍微有一点点罗圈,几天后就得了个外号“掐钩”。在兵团待过的人都知道掐钩,那是抬原木用的专用工具,外形如两个相对的弯月,上端月尖相绞。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就像漫画,有点损,但特点抓住并突出了。
男生就是爱耍这么点歪聪明。

下乡时的施老师
施老师比较傻,思想简单,在兵团呆了六年,不怨天尤人也不投机取巧。不像我等总为前途愁眉苦脸、夜不能寐。她觉得别人能待在这儿我就能,就算是最后在这儿安家落户、生儿育女。
傻人有傻福啊,农工干了没多长时间,选女拖拉机手,居然把她挑上了。连里也不知咋想的,就她那个身高,坐在驾驶楼里,不知道的从前边看还以为是无人驾驶呢。更搞笑的是发动车,东方红链轨拖拉机是柴油发动机,启动时先要把一个小汽油启动机发动着,再由它带动柴油机点火。那小启动机要人力启动,用绳子绕在一个轮子上猛地一拽,带动汽油机。这一拽劲儿不算太大也不小,施老师人太小劲不足,不是被绳子带着反弹回去险些一头撞到车上,就是用力过度一屁股坐到地上。总之,最后她从未启动成功过。
穿上机务工作服不到一年,因为兵团个别现役军人欺辱女知青,毙了两个团级军人。防患未然,女拖拉机手都下岗了。
她被分到科研班,经常跟着农业技术员大陈伺候那几亩试验田。人多地少、精耕细作,活儿肯定轻松啊。科研班都是女知青,我那时是既羡慕又嫉妒:凭啥科研都得是女的?都是“文革速成初中”,咱识字说不定比她们还多几个呢。

业余文艺爱好者,右起:施老师、凤鸣
最后她居然又被推荐上学,哈尔滨师范学校,不但回到哈尔滨而且学校就在她家旁边。我有时候和她开玩笑:你得感谢“四人帮”啊,没有文革你能上学?
施老师算得上生在教师之家。他们家除了她父亲,第二代只要是上学的,都是师范院校。哥哥、姐姐、姐夫、弟弟、弟妹一律都是老师。二哥还是北师大毕业的特级教师,名字上了百年校庆的铭墙。可虽然施老师是他们姊妹中学历最低的,但只有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体育。
她父亲是师大的体育系教授,上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辗转来到东北,是黑龙江省体育界资格最老的几人之一。我看过她父亲的简历,经历复杂,但基本没离开学校。尤其是解放前,落魄的时候在小学教书,风光的时候当过好几年国高(国立高中)校长,那个年代东北一共才有几所国高?标准社会名流啊。最搞笑的是,简历都要有证明人,有一段时间她爸在东北交通大学任教,证明人居然写的是张学良(那学校受抗日战争影响只存在了几年,但史上有名,学校建筑还是梁启超、林徽因参与设计的,现在只留下了校门。张兼任校长)。我看后暗笑不已,问施老师,你爸这不是故意为难组织吗?你让组织上哪儿搞外调去啊?
不过学历不高没有限制施老师的能力,当体育老师绰绰有余。先是在哈尔滨的中学里如鱼得水,结婚后因我在大庆工作,她毫不犹豫调到那当时的苦寒之地教小学,同样把体育课上得有声有色。而且还曾仅凭一己之力为她所在钻井公司捧回油田女子游泳团体赛第三名奖杯,一战成名。故多次入选大庆游泳代表队,赴其它油田参加石油部职工运动会游泳赛。后来让她当大队辅导员,又弄起了那一片学校中唯一的鼓号队,威风凛凛、鼓号齐鸣,经常被外单位请去助威,很给学校长脸。

《哈尔滨日报》上的施老师工作照(前左)
我调到北京,不能丢下她呀,联系学校,试课一次成功。教了几年体育后又发挥她特长,继续当辅导员。积习难改,又整出个我们这一片学校中唯一的鼓号队。
施老师退休了,鼓号队后继乏人,偃旗息鼓了。毕竟鼓号队是要占用很多业余时间和精力的。
去年孙女学滑冰有些胆怯,于是奶奶重新披挂上阵,以场上女子最高龄(68岁)身份出征陪滑。起初还不肯带护具,大概认为丢身份。到底是老骥伏枥,几个回合把掌骨摔裂了,不过几天后依然带伤上阵…
三年疫情,游泳馆、滑冰场大部都关了。施老师无事可干,只好将多余的精力投入厨房,把锅碗瓢盆擦得锃明瓦亮……

陪孙女滑冰

作者下乡时
作者:王立平,1953年生,北京知青, 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推荐上学离开北大荒,1975年毕业于大庆石油学校钻井专业,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电大物理专业,1993年获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工作于大庆油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单位,高级工程师。2013年于北京退休。
来源:新三届
(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