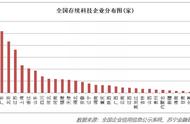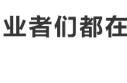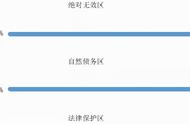大学里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有着非常高的科研水平,他们或许有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换为商业机遇的创业热情,但却面临着大学教职和创业机会之间的权衡。怀揣创业梦想的STEM学者很难找到支持,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本文来自编译,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尤妮斯·杨(EUNICE YANG)第一次尝试创业是在她20多岁的时候,当时她帮助家族经营纸箱制造业务。五年后,在公司被收购后,她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2014年,她已成为匹兹堡-约翰斯顿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终身教授。在护理学院一位同事的帮助下,杨开发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用于预防老年人跌倒(而不是事后检测)。
“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杨告诉我,“如果它在我的脑海中是现实的,如果它能在纸面上运行,而且计算机算法也显示它可以,那么我就不能只呆在匹兹堡大学,把它当作一个研究项目。我需要把它商业化。”
两年来,她一直试图在完成研究和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发产品,但这样的生活根本无法维持下去。最终,她决定休假,18个月后,她辞职并成立了 OK2StandUp 公司,为养老院和其他医疗保健客户提供服务。
杨的故事说明了那些在学术界发展创业兴趣的人所面临的一些挑战,那就是被视为学术界可能并不适合他们。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联席主任露丝·奥克迪吉(Ruth Okediji)说:“学者型创业者通常被老牌的学术界视为可疑人物。”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创意破坏实验室(Creative Destruction Lab)首席经济学家约书亚·甘斯(Joshua Gans)表示,大学是潜在影响力来源的金矿。甘斯补充说:“阁楼里有伦勃朗的作品,”他指的是“世界各地的学者所做的工作能够被商业化”。
以大学为基础的商业化始于1980年,当时《贝-多尔法案》(Bayh-Dole Act)允许美国大学保留教师利用联邦研究经费进行的发明的所有权,并从中获利,利润由学院的发明者和外部合作伙伴分享。从那时起,学术技术转让办公室就成了为创新申请专利和许可证以及生产附带产品的机器,而且这台机器运转良好。终身教职员工通常担任顾问或咨询角色,而学生或其他合作伙伴则领导商业化工作。大学通常允许每周适度的时间津贴或临时请假,让教职工去探索各种机会,并允许向初创企业出租实验室空间。根据代表美国技术转让专业人士的 AUTM 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 124 所 2021 年成立初创企业的大学中,有 92 所大学至少持有一家初创企业的股权。
虽然现有的支持结构对从事创新的教职员工来说还算不错,但对于更多参与创新的学者型创业者来说,却没有长期的路线图,这迫使许多刚入职的学者,最终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蒂芙尼·圣伯纳德(Tiffany St. Bernard)是康奈尔科技大学(Cornell Tech)跑道创业(Runway Startup)博士后项目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目前正处于这个岔路口。她是美发科技公司 HairDays 的创始人,该公司利用计算机视觉提供有关护发的建议。圣伯纳德对于以教员的身份创建自己的公司犹豫不决。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她目睹了具有创业倾向的教授们是如何在两个世界之间挣扎的,即使是在大学推出鼓励创新的举措之际也是如此。她还担心,等到终身教职结束后再创办初创公司,会降低成功的几率。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难有精力和毅力走创业之路。”
学者兼企业家的难处,在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初入职场的科学家,我意识到,对于那些正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决定的人来说,终身教职传递的不仅是一种专业和知识上的归属感,也是一种社会和个人的归属感。终身教职不仅是对卓越研究的一种认可,也是公民身份的一种形式,是希望长期全面参与社会活动的学者的北极星。
但追求终身职位的要求可能很难折衷。创办公司时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尤妮斯·杨(Eunice Yang)指出,虽然研究和创新都可以推进学术使命,但在研究透明度等问题上,这两者可能会发生冲突。“要获得终身教职,你就必须发表文章,要让文章见刊。因此,作为一名学者,如果想经营企业,就不能发表文章,因为你不能把商业秘密发表出来,”她说。这种紧张关系,即使只适用于学者的部分研究,也肯定会带来挑战,除非教师创业被视为大学努力追求卓越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对传统活动的威胁。
另一个障碍是,并非所有的同事都认为创业是一种与学术相容的活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教授希里·布列兹尼茨(Shiri Breznitz)说,学者要想取得成功,同行的认可几乎比大学管理者的认可更重要,因为晋升是由学术部门提出的。其他机构同事的支持信也是大多数终身教职的重要依据。对创业贡献的考量是以个案为基础的,往往受制于不成文的规定,其命运取决于评估委员会的组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同事们对创业追求持怀疑态度。多位参与过终身教职评审过程的学者告诉我,即使是那些在学术研究方面超出预期的人,创业活动也会被视为缺乏专注或奉献精神的表现。因此,对于获得终身教职前的学者来说,从事这类活动是一场赌博,处于这种境地的研究人员可能会背负双重负担,且充满不确定性。
“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和鼓励,”克里斯蒂安·卡塔利尼(Christian Catalini)说,他曾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分校的终身教职岗位上请假,去领导 Meta 已解散的数字货币项目 Diem(前身为 Libra),并最终辞职。他现在是 Lightspark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该公司专注于建立基础设施,帮助企业通过闪电网络发送和接收付款。他说:“如果同事知道你把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实际上可能会影响你的晋升机会。”
另一个挑战是,有些群体从事创业活动的能力较差,或者更不能兼顾。“个体之间有很多差异。总的来说,创业中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学术创业也不例外。如果你是一位年轻的女学者,想要成家立业,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康奈尔科技跑道项目主任费尔南多·戈麦斯·巴塞罗纳(Fernando Gómez-Baquero)说,“如果你是一名移民,对你来说,那么获得终身教职可能意味着你能留在这里,并在多年的移民生涯后真正拥有一个家和一种生活,那么这就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了。”
2013年,时任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校长的戈登·吉(E. Gordon Gee)主张在终身教职制度中采取“多种方式”。这已被用于支持以教学为重点的终身教职任命,但其逻辑有了进一步的延伸。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认识到教学和研究是学术事业的互补贡献者,并接受个人可以专攻。
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俄勒冈州立大学领导的一个联盟最近提出了更系统地认可创新活动的建议,公立大学和土地赠与大学协会也表示支持在晋升和任期决定中考虑技术转让活动。同样,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教授的路易斯·冯·安(Luis von Ahn)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也表示,他支持根据影响力而非论文发表量来激励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想法,那时他与当时的学生塞弗林·哈克(Severin Hacker)共同创办了语言学习平台Duolingo。
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对研究或教学专家的期望,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途径,使教师的创业精神合理化,并减少那些专注于更广泛领域的教师的生活不确定性。与其彻底改变终身教职制度,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创建一个有自己评估标准的教授轨道,允许学者在不同活动(研究、教学和创业)之间合理切换时间和精力。
我们可以把创业者想象成“翻译专家”,他们既从事严谨的研究,又热衷于实践。这不仅有别于传统的以研究为重点的教职,也与“实践教授”或常驻企业家等角色不同,后者通常通过教学和指导将前任(或现任)从业者融入学术界。
调整方向还有助于吸引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新学者。“我感觉到年轻一代有一种更强烈的愿望,希望看到社会更快地使用他们的技术”,并且愿意“放弃一些发表机会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一种权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技术转移中心的教授兼联合执行主任唐纳德·西格尔(Donald Siegel)说。
一种担忧是,奖励创业成就可能会导致研究成果减少。Signal 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玛拉·莱德曼(Mara Lederman)目前正从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学院(University of Toronto’s Rotman School)教授的职位上休假。她表示,大学需要权衡这样一种风险,即提供以创新为重点的激励措施,可能会阻碍实现最大商业突破的基础研究,从而损害商业化努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大学应认真考虑有多少教职员工适合这种模式,并就明确的活动划分达成一致。教职员工在工作重点上的差异是有先例可循的,例如在研究与教学之间进行官方认可的权衡。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以减少教学工作量作为奖励,从而为研究工作提供更多时间。此外,其他领域也存在研究者-实践者的模式。例如,医学院的教师往往将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在倾向于创新的领域创建类似的模式,可以减少学者型创业者面临的质疑。
重要的是要决定计算什么和如何计算。专家和学者型创业者一致认为,在大学眼中,并非所有的创新企业都应被视为等同,或给予同等的荣誉。“我不认为所有创新都是道德中立的,”哈佛法学院的奥克迪吉(Okediji)说,“应该从你用来评估的标准入手,来决定这家公司是否促进了公共利益。”
大学应该为创业应用领域、规模和里程碑提供积极的指导,这样才能发挥机构意义。此外,学分可能取决于所扮演的具体角色。Ropes & Gray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曾担任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高级副校长兼法律总顾问的斯蒂芬·桑格(Stephen Sencer)表示:“参与融资宣传或运营问题,这对初创公司的未来可能非常重要,但这确实不是人们期望的科学领域终身教职员工会做的事情。”他说:“相比之下,初创公司有许多可以直接适用的科学职位。”在评估成功的时候,桑格建议不要只看重商业上的成功,还要考虑运气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以及经济激励与预测一名有价值的教员所具备的素质之间的不一致。此外,并非所有创业者,尤其是非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创业者,都会创办公司或遵循最常见的创业模式。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教授安德鲁·纳尔逊(Andrew Nelson)表示,允许员工灵活地从事其他形式的活动,对于避免强制推行单一的创新模式至关重要。
最后,终身职位的决定是有时间限制的,而创业的成功可能不会在同一个窗口期出现。奥克迪吉说:“有时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会到一项技术的作用:有些技术曾经备受赞誉(例如彻底改变了交通的柴油发动机),但现在却被认为是有害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设置防护栏。大学已经对利益冲突、承诺冲突、大学资源的使用、学生参与、知识产权和所有权等方面的财务和道德问题进行了严格管理。其中一些问题,在创业的轨道下可能会加剧,可以通过谨慎、公平地设计薪酬方案或安排来解决,允许学者型创业者在获取利润之前,根据个人活动的细分情况,偿还部分公共资金。
我们还应努力避免加剧现有的不平等。“你要保持大学是一个平等的空间。因此,如果一个人的技术能为他们带来 2 亿美元,他们就可以比其他人更频繁地不去上课,可以比其他人雇佣更多的研究助理,”奥克迪吉说,并补充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其他资金来源中,如内部拨款。
重新定义学术贡献的结构性灵活性将使大学能够履行其义务,同时提供合法性,吸引有才华的学者,否则他们可能会放弃学术生涯。这也可能使现有的学者型创业者们更有胆量进行更大胆的赌注。
创业本身就有风险,同行和机构的认可只是学者型创业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我们需要释放活跃的脑力来寻求解决方案。不然的话,让那些伦勃朗的画作留在阁楼上实在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