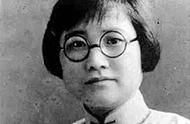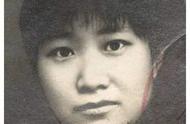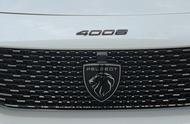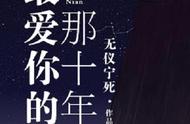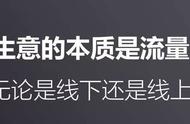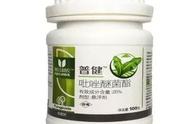中秋月圆,苏雪林对丈夫说:“今天的月亮真圆。”
丈夫看了苏雪林一眼,不解地回答:“月亮再圆,也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
这,便是文学女与理工男地对话。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柴米油盐磨灭人对爱情的幻想。
可对于有些人而言,婚姻更像是一座死死的围城,进去之前没有期待,进去之后满是寂寞。
张爱玲的好友,苏雪林便是如此,一段婚姻,寂寞了一生。

苏雪林,出身于封建大家庭。她的童年,没有私塾,没有新式学堂,所有的文学积累都靠“偷学”。
兄弟上私塾,她在一旁偷上,兄弟们的名著,她家中偷看。18岁那年,她才求得祖母,上了女子学校。
于苏雪林而言,这是接触新世界的机会,但在祖母看来,这是让她学规矩的地方。16岁定下爱的婚约,女子学校毕业刚好嫁人。
可后来,苏雪林以死相逼要去北京上大学,将婚约一再拖延。在北京,苏雪林在思想上成就了全新的自我,追求平等和自由。

作为鲁迅的学生,她也有过激进的观点,令人印象最深的便是,反潮流骂鲁迅。
可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思想叛逆的人,最后在婚姻上妥协。
祖母是家中的“掌权者”,她不许苏雪林上学,一向懦弱的母亲苦苦相求,换得她女子学校的机会;祖母不许苏雪林升学,苏雪林以绝食相比,母亲偷偷送饭,最后祖母也无奈应下。
苏雪林越是激进、越是叛逆,她对始终暗中相助的母亲,便越是感恩。于是,在这种感恩之下,她以“愚孝”心理,听从母亲建议,嫁给了未婚夫张宝龄。

张宝龄,曾留学国外,在欧洲获得工科学位。从学识上看,他与具有新式思想的苏雪林还算相配。
可是,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即便同是新思想青年,但一个工科、一个文科,要想聊到一起,依旧存在很大障碍。
不管婚姻的开始是否拥有爱情,每一对新婚夫妻,都曾尝试国彼此靠近。
当年,鲁迅再厌烦朱安,也依旧尝试与她交流,只不过被朱安接二连三的自欺欺人击退,只能选择离去。
而苏雪林与张宝龄最大的问题,便是太过“实事求是”。

正如文章开头那一幕,中秋佳节,浪漫月光下,张宝龄的一句话直接将气氛降到冰点。她气哄哄地回到房间,这样枯燥无趣的工科男,苏雪林无法接受。
中秋赏月的“煞风景”只是冰山一角,他们是夫妻,还有漫长的几十年要如何度过?
随着婚姻生活的日渐推进,苏雪林与张宝龄并没有越来越熟悉,反而越来越生疏。从最开始的没话找话,到最后的相顾无言。
张宝龄虽然粗枝大叶,但也能感受到枕边人的变化,可他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每一次和苏雪林交谈,大都不欢而散。
顶着夫妻的名份,没有夫妻的情分,他们不过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发展到后期,他们甚至都很少聚在一起吃饭。
后来,苏雪林以工作为由,离开了有张宝龄的城市,一走就是几十年。

后半生的几十年,苏雪林没有再嫁,张宝龄也没有再娶,他们都默契地领养了孩子,定居在不同的城市。
在这场有名无实的婚姻里,苏雪林与张宝龄都没有错,他们只是彼此不合适。
刚结婚时,张宝龄也曾为婚姻做出过努力,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设计了一座船型小洋楼作为爱巢。在张宝龄的期望中,他将会开着爱的小船,与苏雪林一起驶到彼岸。
只可惜,天不随人愿,他们的爱情死在了泥土里,连萌芽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爱情,也就无需打扰,各据一城,安稳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快乐。
多年后,苏雪林得知张宝龄去世,她的心中充满愧疚,未尽妻子义务,天南地北白白耽误彼此一生。
其实,相比诸多民国才女,苏雪林的一生也能算得上幸运。
即便是被包办婚姻,但她遇上的不是封建男子,从未禁锢她的自由。
没有遇上爱情固然遗憾,但这也同时避免承受爱情的伤痛。
萧红因为爱情,一生漂泊,一生漩涡,一生痛;张爱玲因为爱情,被伤得遍体鳞伤,异国寻温暖。
万物有得失,缺了爱情,有了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