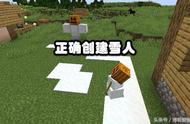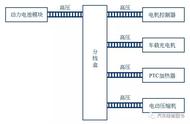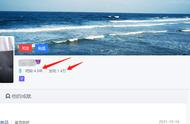有人说,每个四川人的故乡记忆,都与一条河有关。“千河之省”四川,近三千条大河以及无数条小河,如同大大小小的血管,滋养着富庶的“天府之国”。在众多的水系中,发源于川西北九顶山南麓的沱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流经四川的2.55万平方公里,是蜀地城镇最集中、人口最密集、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承载了全省25%以上的人口和30%以上的GDP。
对沱江的保护
四川立足生态禀赋
以单独流域立法的方式推进污染治理
以河长制促进“河长治”
从生态修复迈向长久保护
清河、护岸、净水、保水
让沱江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流域立法推进水污染治理
2004年3月,一起特大水质污染事故使美丽的沱江变成了一条哭泣之河。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对这起事故认定为: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最大的一起水污染事故。
“沱江流域的问题,涉及源头控制和流域体制机制,需要上下游跨界协同作战,统筹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并通过立法来解决。”业内人士一致认为。
2018年9月底,《沱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签署,按照“保护者得偿、受益者补偿、损害者赔偿”的原则,从2018年至2020年,沿岸7市每年共同出资5亿元,设立沱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资金。
2019年9月1日,四川省首次以单独流域立法的方式推进《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
《条例》突出了饮用水水源保护,体现了不抵触、可操作等特点。其中,规定了生态保护补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四项基本制度。同时,授权四川省政府制定生态保护补偿和排污权有偿使用交易具体办法。
从“九龙治水”到“一拳发力”
沱江之畔的内江花萼湿地公园一角,一块2009年下半年制作的提示牌上记录着四川最早一批河长的名单和联系方式。那一年,在借鉴无锡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内江在四川率先启动了河长制试点。

河长制给饱受沱江污染之苦的内江人带来了什么?
“治水项目执行落实的速度不断加快。”作为全省最早一批河长,内江资中县重龙镇党委*、沱江重龙镇段乡级河长刘衡说,效果立竿见影,治水规划不再“只停留在纸上”。
2017年,沱江被列入四川省十大主要河流,明确由两位省级领导担任沱江河长。各市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分段河长,设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责任体系,实现从“九龙治水”到“一拳发力”。
在河长制体系下
沱江流域的一河一策保护治理方案出炉
沱江流域7个市29个县市区划分为15个单位
整体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各地自然资源部门对影响沱江流域水环境、生态环境的重大建设项目,严格进行规划选址及用地预审审查。推行动态巡查责任制,建立自然资源网格化监管体系,结合“河滩地整治”专项整治行动,对沱江流域违法用地、违法采矿等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并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对沱江流域自然资源违法行为进行全面监管,将违法行为发现在萌芽、遏制在初始。
生态修复还一江碧水
在什邡市蓥华镇仁和村内,一条木制栈道沿山脊逶迤而上,栈道两旁已种满茵茵绿草,曾经的磷石膏渣场已成为与周边群山融为一体的观景高台。

“这里曾经有三座巨大的磷石膏堆,如同三座大山,最高的达到50米。巨大体量的磷石膏堆放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部分出现滑坡、垮塌,甚至存在磷石膏下河的风险。” 什邡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什邡市全面打响了以穿心店磷石膏堆场治理工程为重点的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治理并非简单地将磷石膏堆搬走,而是通过堆体削峰、覆膜导流、盖土植绿等一系列举措,让整个堆场得到全方位整治。
整个工程累计挖填磷石膏约163万立方米、削坡28万平方米,新建河道挡墙617米、修复原破损河道挡墙170米;累计平整、硬化地块3.2万平方米,覆土14.8万平方米,新建地下水监测井5口。同时开展覆土植绿,借古韵古味的历史文化,打造一个连接城市与自然、融合历史与现代的体育休闲公园。

据了解,2019年至2020年,四川省共投入资金1.6亿元用于支持沱江流域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完成修复面积945公顷。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整治环境是还历史欠账,更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2020年,沱江16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
由“十三五”初期的12.5%
提高到2020年底的93.8%
创近20年来最好水质
刮骨与疗毒,涵养与善待
重塑了沱江水清岸绿的旖旎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