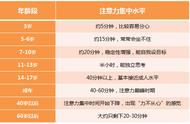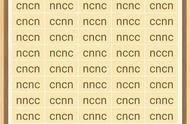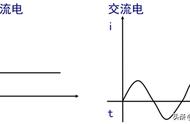治病的日子(一)
三伏天埋沙去
车子载着爸爸、姐姐、妻子,一家人搞的像旅游一样,把我送到了吐鲁番沙疗所。直接拒绝了妻子的陪伴,独自留下准备沙疗。
吐鲁番的三伏天,气温高达40度以上,地表温度早己超过80度。你在沙子里放个鸡蛋,一会就可以剥开皮直接吃。
沙疗所,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大的院落,一大排平房,有大概二十个左右独立的标准客房,有卫生间但没有洗澡的设施。房子与沙池隔着葡萄长廊。靠近大门的位置就是食堂,门口放着几张大桌子、长条板凳。
来埋沙的人先在沙疗所院里的沙池挖个坑,让太阳晒一阵子。男的穿个裤头,女的穿个长裙,把裙子拉起放在肩部,露出个头。跳进沙坑,或躺或坐,陪同的人快速用铁锹把沙子厚厚的覆盖在身体裸露的部位。每个人头部都用遮阳伞挡着刺眼的烈日,手能够着的地方放个特大号的烧水壶,里面满满的灌着凉开水或茶,配上个碗或杯子。这是埋沙的序曲,适应一下埋与陪的人之间的默契程度。因为真正的沙疗在一大片沙滩中,那里有几个名字特别好听的沙丘,什么英雄沙丘、爱情沙丘……
傍晚时分,一辆辆毛驴“的士”拉着从外面沙疗回来的人,一个个脸上晒的通红,汗流浃背。一眼望去,有的男人几乎光着膀子,女人穿着吊带衫,打着小阳伞手里摇着扇子,有的男男女女则穿着厚厚的绒衣、毛衣甚至冬天的棉袄捂着厚围巾戴着棉手套。
吃饭的时候到了,泾渭分明,光着膀子穿着裙子的都捧着西瓜躲在阴凉处,那些穿着奇葩的则端着大碗(严格说是盆,和我家面盆一般大)坐在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着清炖羊肉或拉条子。这里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怪异。
回到房间,好像进了蒸笼,只好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的葡萄架下。隔壁房间也开始入住新的客人,不一会大家就彼此熟悉了起来。一对来自博乐的快七十岁的夫妻,男的姓张,是陪着老伴来治疗的。还有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的中年退伍军人。沙疗所的一位维吾尔族中年女人,简单地用汉语给我们交待些注意事项,明天开始,为期十五天的沙疗,在这期间不允许洗澡。然后她盯着我和退伍军人说“一个人不行,埋沙必须要有人陪着”。我和退伍军人彼此上下打量了番,决定搭伴相互帮忙,明天直接上英雄沙丘。
第二天上午11点,我们新来的三家,四个人,提着铁锹、伞、水、浴巾,坐着毛驴“的士”开心地奔向沙滩。
毛驴车沿着村里的土路,穿过一个特别大的村庄集市,向沙疗的方向行驶。绿州的景色很快消失,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沙漠,沙漠上有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和正在挖坑的人,看上去人头攒动特别壮观。沙漠边上有为数不多古老的大树,绿色的树荫下星星点点地坐着些人。赶毛驴车的小伙子指着前面的沙丘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英雄沙包(丘)”,便把我们放在了一棵大树下面。
四个人开始兴奋的找位置,扎伞、挖坑。埋沙的沙坑是有些要求的,必须把病变部位全部埋入沙土中。愽乐的老太太个子不高,但胖。复转军人比我稍矮一点,但体型保持的很好。我,178的身高,体重足足110多公斤。三个人都必须是全身平躺进沙坑只露头和心脏以上的部分。顶着烈日开始战斗,也许是第一天上阵,个个干劲十足,不一会把三个长方型身高体宽合适,大概40—50公分深的沙坑便刨好了,摸摸了坑里的温度还能接受,逐个的试试坑的大小,结果给我刨的坑,人只能侧着,根本平躺不了。三个人大汗淋淋继续开挖,坑挖好了,回到大树下喘口气,让太阳把沙坑晒一会。复转军人是个热心肠,他决定先难后易按顺序埋,我、老太太、他,这样他和老张就肩负起了填埋沙土的使命。填埋沙土不仅需要体力还得有点技术,因为沙子的温度己远超过人的皮肤可接受的程度,必须在极短的时间,达到很厚很深的覆盖,人身体内的水分瞬间排出,变成热蒸层才能安全。如果填埋速度和沙土的量达不到要求,很容易发生烫伤。
我第一个把牙咬上,闭上眼睛平躺入坑。复转军人、老张、老太太三个人轮番挥锹一阵疯狂的填埋。老太太入坑,复转军人、老张再一次疯狂。埋好老太太,老张示意先歇会,因为接下来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战斗。好在,一切顺利。大家都埋好后,老张轮流着给躺在坑里的三个人倒水,关切地询问着感受。
一开始,因为过于紧张,除了感觉烫、热、喘不上气,也顾不得其他。不一会就觉得自己被活活地放上蒸笼了,全身的水份似乎都被大地吸干了,喉咙着火了一样。不停地端起大碗,喘气、喝水,喝水、喘气,短短的十几分钟,如同熬过慢长的一段时光……
“十五分钟了”,老张大声的喊着,我们各自挣扎着从沙坑里起身,快速地用干沙土把湿漉漉的粘在身上的泥沙擦掉,裏上浴巾,连滚带爬地回到大树下,狼狈不堪。
离开沙坑,坐在树下,就觉得四周都凉风习习,赶紧的穿衣。正午的阳光开始直晒下来,一辆辆毛驴车开始忙碌的接人回去吃午饭。坐上毛驴车,再次驶过村庄集市才注意到喧闹的吆喝声,顺着声音望去看到了各种小吃的摊位和熙熙攘攘穿行在其中的人流,有搭在道路一侧的露天床铺,也有村民们开办的家庭旅馆,这里正是一年中埋沙季节人最多的时候,天南地北而来的人绝大多数都选择在此落脚。后来才知道,每年有数万人来这里感受传统的沙疗。
按照要求,每天的沙疗需要上午、下午各一次。上午结束,人己经乏的没了精神,身体像被什么掏空了似的,毫不犹豫地点了一盆清炖羊肉一个馕,一口气吃完。唯独老张啥也咽不下去,端个水杯,不停地喝水。
吃完饭,妻子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直接告诉她,赶紧的请上半个月的假,今晚上就来。
下午出发的时候,复转军人和老太太商量“咱们先埋个下半身,实在没力气了……”。
妻子赶来了。火州的三伏天我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冷,房间连门窗也不敢开了。那一夜开始,每天晚上妻子、老张放着床却闷热的睡不成,只能各自搬个椅子在葡萄架下打个旽。白天乘我们穿着绒衣裤在屋外聊天的时间,赶紧的打开门窗透透气睡一会。也就从这一天开始,妻子变成了这支队伍挖坑填埋的主力。我们三个埋沙子的人既不沾水又不洗澡、既不开门窗又睡的跟死人一样,房间里开始弥漫着一种特殊的体味。
埋沙的日子枯燥且慢长,复转军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副麻将,几个人凑了一桌,每天晚上沙疗所的葡萄廊下,昏暗的一盏灯光中,四个穿着毛衣、绒裤、戴着线手套的人开始了另一番战斗。
埋沙的日子快结束了,最后一天的上午,坑也挖好了,人也躺下了,我己习惯性地自己倒水,慢慢喝。突然,旁边一个人惊叫着从沙坑里飞了出来。妻子、老张手里拿着铁锹吓的直愣愣站着,只见复转军人抱着一条腿在沙滩上打转,带着哭腔大声的吼道“把皮烫下来了!”想想看,十几天了,在这样的高温下,吃不下,睡不了,妻子、老张也己没有了力气,或许有一铲子沙土少了,也或许挨到第三个埋他,速度慢了一拍,总之,他被沙土烫伤了。好在看上去红的面积不很大,皮也只掉下来一小条。回到沙疗所,医生给涂了点药,没有什么问题。
第十五天,沙疗所让我们去洗药浴,高兴的一奔子跑去,结果进去一看,头顶上吊着一个小桶桶,打开开关,如同小孩尿尿似的一小股中草药味道的黄水水流了下来……
第十六天早晨起床,准备返程,沙疗所那位维吾尔族中年女人走过来,反复叮嘱“为了保证埋沙的效果,最好去艾丁湖去洗洗。”一听艾丁湖就觉得一下子爽了,几个埋沙的人都挤到一辆车上,顺着沙疗所给的路线,一会儿便到了。艾丁湖、艾丁湖,这那里是什么湖,在一大片盐碱地的中央,一大块、一小块的分布着些泛着黄,甚至颜色发黑的,冒着特别奇葩味道的浅浅的“臭水”。不远处,男男女女的在不同颜色的臭水滩中尽情的洗浴,享受着“天体浴”。啥脾气也没有,自个找个地方,脱光衣服,躺进烫人的黄浆浆里……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