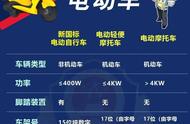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一代人总是摧毁上一代人所构建的东西,一代人所确立的东西总是被下一代人所毁灭。只 有在数学领域,每代人都是在老建筑之上构建新楼层。
分析学,无穷过程的研究,曾经被牛顿和莱布尼茨理解为涉及到连续量,比如长度、面积、速度和加速度,而数论则明显以离散的自然数集作为它的领地。群论起初只涉及到离散的元素集,但克莱因想到了把数学的离散方面和连续方面在群的概念下统一起来。19世纪确实是数学中互相关联的一个时期。对分析学和代数学的几何学解释是这一趋势的一个方面;把解析的技术引入到数论领域是另一个方面。到19世纪末,最强大的趋势是算术化;它影响了代数学、几何学和分析学。
哥廷根大学有两个年轻人深受狄利克雷的影响,尽管他们在个性和数学方向上大相径庭。一个是理查德·戴德金;另一个是波恩哈德·黎曼。
黎曼在哥廷根
黎曼接替狄利克雷的位置时,他已经发表了5篇专题论文,其中两篇是论述物理学问题。我们将援引黎曼最短的、大概也是最著名的一篇论文的实例,然后指出他对数学物理学的贡献。
黎曼还得出了一些很有深度的跟数论和古典分析学有关的定理。欧拉曾经注意到素数理论与下面这个级数之间的关系:

式中,S是一个整数,这是狄利克雷级数的一个特例。黎曼阵对S是一个复变量的情况研究了同样的级数,级数的和被定义为一个函数zeta(S),打那以后,这个函数被称作黎曼zeta函数。黎曼是个多面手,有着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他不仅对几何学和数论、而且还对分析学做出了贡献。在分析学领域,他因为在积分定义的精炼上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对柯西—黎曼方程的强调,以及因为黎曼曲面,而被人们所铭记。这些曲面是一个匠心独运的方案,为的是让一个函数具有一致性,亦即,表示一个复变函数的一一映射,而这样的函数在平常的高斯平面上是多值的。
这里,我们看到了黎曼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分析学中一种有着强烈直觉的几何学背景,与魏尔斯特拉斯学派的算术化趋势形成鲜明对照。他的方法被称作“发现的方法”,而魏尔斯特拉斯的方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是一种“证明的方法”。他的成果极为重要,以至于伯特兰·罗素把他描述为“逻辑上是爱因斯坦的直接前辈。”正是黎曼在物理学和数学上的直觉天才,使得像黎曼空间曲率或流形这样一些概念得以产生,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广义相对论是不可能被构想出来的。
数学物理学
19世纪最早对数学物理学做出贡献的,是爱尔兰人威廉·卢云·哈密顿,他大量利用了他在1820年代晚期建立数学光学理论时发展出来的概念,其方法的关键是把变分原理引入到了某些偏微分方程的处理中。他的研究建立在拉格朗日和泊松的工作的基础上,但利用了更早确立的一些物理学原理。雅可比在19世纪30年代打造出了他自己的动力学,重塑了哈密顿的创新观念,并在他自己的理论背景下关注它们。结果是如今所谓的哈密顿—雅可比理论。哈密顿的主要支持者是苏格兰物理学家彼得·格思里·泰特(1831~1901)。他的数学贡献包括早年对结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他遵循了一条由高斯和利斯廷开创的不大为人所知的研究路线,得到了电力学研究的促进。
乔治·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的名字每一个研读高等微积分的学生都耳熟能详。1850年,斯托克斯证明了斯托克斯定理。麦克斯韦最有名的是他在电磁波动方程求导上所取得的惊人成功,他在促使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使用向量上发挥了很大影响。
魏尔斯特拉斯
在19世纪下半叶,柏林最重要的分析学家是卡尔·魏尔斯特拉斯。1854年,魏尔斯特拉斯发表在《克列尔杂志》上的一篇论述阿贝尔函数的论文使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在19世纪最后30余年里,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分析学家。
在19世纪中叶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无穷级数在某个区间内收敛于一个连续而可微的函数f(x),则通过逐项求原级数的微分所得到的第二个级数在同一区间必定收敛于函数f'(x)。有好几个数学家证明,情况未必是这样,而且,只有这个级数对于这个区间是一致收敛的。魏尔斯特拉斯证明了,对于一个一致收敛的级数,逐项求积分也是允许的。1870年,海涅证明,一个连续函数,如果你把一致收敛这个条件强加给它,则它的傅立叶级数展开就是唯一的。在这方面,他消除了狄利克雷和黎曼论述傅立叶级数的作品中的困难。
魏尔斯特拉斯对分析学的重要贡献之一被称作“解析延拓”。魏尔斯特拉斯把解析函数定义为一个幂级数连同所有那些可以通过解析开拓从它这里获得的级数。像魏尔斯特拉斯所做的这种工作,其重要性在数学分析中尤其能够感觉到,在这一领域,微分方程的解很少是以不同于无穷级数的其他形式求出的。
分析学的算术化
1872年是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不仅在几何学领域,而且特别是在分析学领域。在这一年,至少有5个数学家对分析学的算术化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其中一个是法国人,其余的是德国人。这个法国人是勃艮第大学的夏尔·梅雷;4个德国人分别是:柏林大学的卡尔·魏尔斯特拉斯,哈勒大学的H.E.海涅和格奥尔格·康托尔,以及不伦瑞克大学的J.W.R.戴德金。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半个世纪函数和数的性质研究的高峰,这项研究是1822年随着傅立叶的热理论以及马丁·欧姆的努力开始的,同一年,欧姆在《论完全一致的数学体系》中试图把整个分析学简化为算术。
这50年的焦虑不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对无穷级数上执行的运算缺乏信任。人们甚至都不清楚,函数的无穷级数———例如,幂级数,正弦或余弦级数———究竟是不是始终收敛于它所源自的那个函数。第二个原因是“实数”这个术语缺乏任何定义所引发的忧虑,这个定义是算术化计划的核心。到1817年,波尔查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分析学中严谨性的必要,以至于克莱因把他称作“算术化之父”;但波尔查诺的影响比不上柯西,后者的分析学依然受到几何直觉的妨碍。就连波尔查诺在1830年前后提出的连续不可微函数也被后来者所忽视,魏尔斯特拉斯所给出的这种函数的实例,被普遍认为是它的最早例证。
与此同时,黎曼展示了一个函数f(x),它在一个区间内无穷多个点上不连续,然而它的积分却存在,并定义了一个连续函数F(x),对于上述无穷多个点,它并没有导数。黎曼的函数在某种意义上比波尔查诺和魏尔斯特拉斯的函数更正常一些,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积分需要一个比柯西的定义更为小心谨慎的定义,柯西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条曲线之下的区域这样一种几何感的引导。今天从上和与下和的角度对一个区间上的定积分给出的定义,通常被称作黎曼积分,以纪念这个给出有界函数可积的充分必要条件的人。例如,狄利克雷函数在任何区间上都没有黎曼积分。更一般的积分定义,加诸函数的条件更弱,是在下个世纪提出的,但大多数大学微积分课程中所使用的积分定义依然是黎曼的定义。
在波尔查诺的工作与魏尔斯特拉斯的工作之间,存在一段大约50年的间隔,但在这半个世纪里人们的努力是如此一致,对重新发现波尔查诺的作品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有一个著名的定理被冠以这两个人的名字,这就是波尔查诺—魏尔斯特拉斯定理:一个包含无穷多个元(比如点和数)的有界集S至少包含一个极限点。尽管这个定理是波尔查诺证明的,而且柯西明显也知道,但正是魏尔斯特拉斯的工作,使得它被数学家们所熟悉。
拉格朗日曾对傅立叶级数表示怀疑,但1823年,柯西认为他已经证明了一般傅立叶级数的收敛性。狄利克雷让我们看到,柯西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并提出了收敛性的充分条件。黎曼正是在试图放宽狄利克雷提出的傅立叶级数收敛性条件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他对黎曼积分的定义;关于这一点,他证明了一个函数f(x)在一个区间内可积,而无需可被傅立叶级数展开。正是无穷三角级数的研究,导致了康托尔的集合理论。
在决定性的1872年刚刚过去一年之后,一个有望对数学和数学史做出重要贡献的年轻人去世了,当时只有34岁。他就是赫尔曼·汉克尔,黎曼的学生和莱比锡大学的数学教授。1867年,汉克尔出版了《复数系理论》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建立一种泛算术的条件因此是一种纯智性数学,一种脱离了一切感觉的数学”。我们已经看到,当高斯、罗巴切夫斯基和波约使自己摆脱了空间成见的时候,几何学的革命便发生了。在有点类似的意义上,正如汉克尔所预见的那样,只有当数学家们懂得,实数应该被视为“智性结构”,而不是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那里继承来的从直觉上给出的量,分析学的彻底算术化才成为可能。
魏尔斯特拉斯试图把微积分跟几何学分离开来,把它仅仅建立在数的概念的基础之上。要做这件工作,就必须给出独立于极限概念的无理数的定义,因为迄今为止前者依然以后者为先决条件。为了纠正柯西的逻辑错误,魏尔斯特拉斯通过使数列本身成为数或极限,从而解决了一个收敛数列的极限是否存在的问题。
康托尔与戴德金
戴德金早在1858年就开始关注无理数问题,当时他正在讲授微积分。他得出结论,极限概念,如果想让它严谨的话,就应该仅仅通过算术来发展,无需来自几何的引导。戴德金没有简单地寻找一条走出柯西的恶性循环的途径,而是问自己,在连续的几何量中,究竟有什么东西把它跟有理数区别开来。
伽利略和莱布尼茨认为,直线上点的“连续”是它们的密度的结果———在任何两点之间总是有第三点。然而,有理数也有这个属性,但它们并没有构成一个连续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戴德金得出结论:一条线段的连续性,其本质并非由于一种含糊不清的紧密相连,而是要归因于一种截然相反的属性:线段上的一点把线段分为两部分的那种特性。把线段上的点分为两类,使得每一点属于且只属于其中一类,且一类中的每一点都在另一类中的每一点的左边,在任何这样的分割中,都有且只有一点导致这种分割。
戴德金认识到,可以把有理数域扩大,构成一个实数的连续统,只要你假设一个前提,这就是如今所说的康托尔—戴德金公理,即:一条直线上的点可以跟实数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戴德金指出,现在,关于极限的基本定理都可以得到证明,而无需求助于几何学。正是几何学,指明了通向连续性的恰当定义之路,但到最后,它被排除在这个概念正式的算术定义之外。有理数系中的戴德金分割,或实数的等价物,如今取代了几何量,成为分析学的支柱。
实数的定义,正如汉克尔曾经提及的那样,是建立在有理数基础上的智性结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给数学的某种东西。在上述定义中,一个最流行的定义是戴德金的定义。20世纪初,伯特兰·罗素对戴德金分割提出了修改。
康托尔出生于圣彼得堡,在苏黎世、哥廷根和柏林上学期间,专注于哲学、物理学和数学———这个过程似乎培养了他前所未有的数学想象力。1867年,他以一篇关于数论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但他的早期作品却显示出了对魏尔斯特拉斯的分析学的兴趣。这一领域促使他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头脑里迸发出的那些革命性的观念。我们已经提到过康托尔跟“实数”这个平淡无奇的术语有关的工作;但他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以“无穷”这个刺激性的词语为中心。
自芝诺的时代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无穷,既在神学领域,也在数学领域,但1872年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他所谈论的是什么。在关于无穷的讨论中,人们太过频繁地援引的实例,都是诸如无穷次幂或无穷大量之类的东西。偶尔,像伽利略和波尔查诺的作品那样,人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一个集合的无穷多元上,例如,自然数或一条线段上的点。在人们一直试图识别出数学中实际的或“完全的”无穷,在这样的努力中,柯西和魏尔斯特拉斯只看到了悖论,并相信无穷大和无穷小所指称的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可能性———即上述过程的不完全性。康托尔和戴德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波尔查诺的悖论中,戴德金看到的不是反常,而是无穷集的一个普遍属性,他把这一属性视为一个准确的定义:
一个系统S,当它与自身的严格意义上的一部分相似时,我们说它是无穷的;在相反的情况下,我们说S是一个有限的系统。
用更现代的术语说,一个元素集S,如果它的一个真子集S'中的元素可以跟S中的元素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则我们说S是无穷集。
戴德金的无穷集定义1872年发表在他的《连续性与无理数》中。1874年,康托尔在《克列尔杂志》上发表了他最具革命性的论文之一。他像戴德金一样,也认识到了无穷集的基本属性,但是,不同的是,他认识到,并非所有无穷集都是一样的。在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同的元素集可以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就说它们有一样的数量(基数)。以有点类似的方式,康托尔着手依据集合的“势”来构建无穷集的等级体系。完全平方数集或三角形数集跟所有正整数的集合有同样的势,因为这些集合可以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些集合似乎比所有有理分数的集合小得多,然而,康托尔证明,有理分数的集合也是可数的,也就是说,它也能跟正整数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有同样的势。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循着下图中的箭头,顺着箭头的方向“数一数”分数。

有理分数非常密集,在任何两个有理分数(不管它们挨得多近)之间,总是还有一个有理分数;然而,康托尔的排列显示,分数集的势跟整数集是一样的。你一定很想知道,是不是所有数集都有同样的势,但康托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情况并非如此。例如,跟有理分数的集合比起来,所有实数的集合有更高的势。为了证明这一点,康托尔使用了归谬法。假设0与1之间的实数是可数的,表示为无尽小数(例如,1/3是0.333…,1/2是0.499…,以此类推),并以可数顺序排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