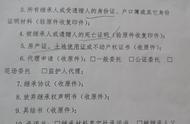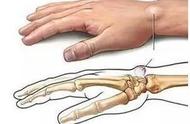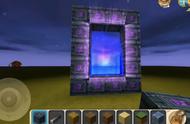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脸叔。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宅家的这段日子,我看了不少感情类的书和剧,发现这句话说得不那么准确:出问题的从来都不是婚姻,而是人。
爱你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会爱你。

中秋节那天,轮到我们组值白班,看着一屋的病人,我不由想起了入科第一天的场景。
头天报道,周老大掐着腰站在门口:“欢迎各位来到抢救间,我科无值班补贴;无年节福利;365天节假日不休;不得请假;不得旷工,否则扔回训练处接受总带教再教育——有人有意见吗?”
如他所说,急诊不存在任何法定节假日,别说今天是中秋,就算是年三十,轮到值班的组也得一个不落地蹲在岗上。
不过也看运气,今早刚下夜班的人可以回去歇两天一夜,正好回家过节,而我们这些刚上白班的同事,不仅今天要打一天仗,明天晚上还要再干一整宿,中秋三天没一天好歇。
此刻老大的气场一如当初的威武雄壮,手里的一大摞材料在门框上拍得啪啪直响,“一大早都拉着个脸!干活去干活去!大过节的,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刚下夜班的带组老师从老大身边挤出门,他喜气洋洋地拍着老大的肩膀:“哎呀,老周,中秋娃娃们肯定惦记着回家,上班哪有动力呀,你要理解。”
老大盯着夜班带组老师笑得见牙不见眼的脸,矜持地挥着材料把他打出了门。眼看老大心情不好要遭池鱼之灾,我赶紧拖着还在呆呆看热闹的程师姐逃离现场。
程师姐大名程瑗,是我刚入科时的带教,工作起来一丝不苟,搞科研也是一方大将,奈何反应总是慢半拍。
早交班时间电脑都是抢手货,幸亏跑得够快,我们俩才一人霸占一台电脑坐了下来。
交班时我收了个车祸病人,打开电脑急吼吼地打了一堆输血的单子给家属签字,扯过话筒喊了几遍病人名字,家属却不知去向。我朝谈话区背面的拐角又扯着脖子喊了半天,依然没人搭理我。
程瑗搂着键盘“噼里啪啦”地打字,等敲完半页纸按了打印,才刚睡醒一样转头,“你是喊车祸伤那个吗,我瞧见他家属往收费处那边去了哈。”
我早习惯了她的反射弧,哭笑不得地谢了她,卷起一摞签字单就去抓家属。还没到收费处,就被人拉住了衣角。
我低头,一个小孩儿拦在我身前,肉滚滚的小手使劲拽着我的衣角,忙不迭地冲身后叫着:“爸爸爸爸,医生在这儿!”
还没等我开口,前面的走廊拐角就“噌”地出来一个男人,准确来说是两个——男人背上还背着一个女人。
男人脸上是难以掩饰的焦灼,他腾不出手来擦头上的汗,把女人往上颠了颠,问我:“您好您好,请问在哪挂号?”
男人中等身材,弯腰背着人正好和我差不多高度,背上的女人靠在他肩头,头发遮着脸看不清面色,只从四肢上看得出身形微胖,一时间也看不出是什么毛病。
我赶紧指着走廊那一头:“那儿,拐弯儿就是。”
小孩头顶上两个揪揪一晃,撒开我的白大褂冲出去,背着媳妇儿的大哥一边跑一边向我道谢。我挥挥手,正看见车祸伤的家属从前面过去,立时将这家人暂时抛到脑后,追上去要签字。
取血单搞定,我总算松了口气,正猜刚才那个女人是什么问题,是走专科急诊还是直接进抢救间的时候,工作群“叮”地一响。
老大:@王婧 在哪,赶紧来收病人。
我快步穿过走廊,推开抢救间的门,看见刚才那对父女,妻子已经临时安置在床上,丈夫正忙不迭地在兜里掏着什么。
小女孩并不闹,乖乖拽着爸爸的衣襟,一双黑黝黝的眼睛骨碌碌转着,伸长脖子往里面的床上瞅。
见了我,男人礼貌地笑了笑,我点点头,看样子老大已经问过了病史。我从老大手里接过刚打好的床头单挂上去,瞟见上面的信息,怔了一下。
宋芳,女,34岁,拟诊,肺栓塞。

嘱咐家属去买住院用品之后,我仔细去看了一遍患者的情况:患者突发胸痛、呼吸困难入院,没有叫救护车,丈夫直接打了车一路把她背到我们医院。
虽然患者平素体弱,时常乏力,但并没有相关的就诊资料可以参考。
趁家属去买东西的空当,我打印了所有的签字单,刚刚完工就看见一大一小两个人影提着大包小裹地往谈话窗口跑过来。
大人和孩子都是一头汗,大哥把手里的几个袋子连同孩子拎着的小塑料袋一块交给我:“辛苦您了,麻烦您帮忙带进去……”
我一手接过沉甸甸的袋子,一手把签字单递过去:“客气了,您先签着,不明白的地方等会我给您解释。”

提着东西的镜子
大哥忙不迭地点头,从口袋掏出一袋巧克力豆,闺女嘴里塞一个,自己吃一个,开始研究起签字单上的内容。我拎着东西进了抢救间。
抢救间分为A、B、F三个区,A区收治的大都是情况紧急随时可能抢救的病人;B区则主要收治病情较为稳定的,或者A区里已经好转的病人;F区只有唯一的一张床,平时病人再多都是空着的,而一旦有人,就意味着今天科里十有八九要出一份死亡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