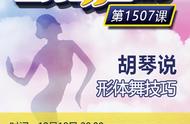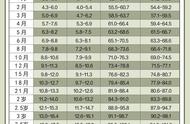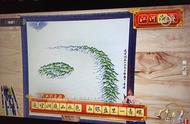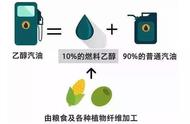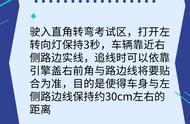干板腔流传在运城方言区这一带。出场的演员一至二人,可以单口,可以多口,群口的不多。干板腔就是没有伴奏没有唱腔的押韵说白,和快板有点像,以说为主,不同的是略微讲究一些故事性。故事大多是搞笑调侃。有大段子,也有小段子。小段子三言两语,长一点的段子,也可以说上好半天。由于都用本地方言说故事,押当地的方言韵,这一块人特爱听。干板腔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拉开场子就能说,自家的东西,本地人就是待见。
集体化时代,我在村里劳动时,经常听到巷子里的红脸森娃给大家说《卖膏药》。段子很长,说的是一个卖假药的江湖医生行医被惩戒的故事。假医生乱卖虎狼药,被告到官府,受了鞭刑。县官升堂问他膏药用什么原料,假医生对——
“虼蚤屎,蚂蚱尿,蛤蟆尾巴鲤鱼漂。蚂蚂蚍蜉籽蛋,媳妇子本钱。”
后面的两种,籽蛋指公蚂蚁的睾丸,世上哪里有?不过搞笑。媳妇子本钱,当然说的女人的羞处。哪里能找到这号药材?
疗效呢?贾医生说——
出北门,上北坡,新坟总比老坟多,新坟都是我害死,老坟吃的师傅的药。
县官给了责罚。江湖医生告白——
“待别人四碟八碗,待我是藤条木鞭杆,扳翻,拽展,按一按稀软,连打四十大板,从此再不敢提卖膏药一款。”
红脸森娃早已去世多年,他早年在西安点心铺子里当伙计,粗通文墨。这个段子,从民国年代村里就开始说,一直说到集体化。前些年我回去过春节,村里闹社火,还有人翻出红脸森娃的《卖膏药》凑热闹,这个已经明显的不合时宜,不过乡亲们还是爱听。

乡下有的是编写干板腔的高手。高头村的邻村张岳村,有一个小伙,编了很多段子。附近迎亲娶媳妇的,经常拉他来演出助兴。这里娶媳妇的人家,新媳妇进了大巷,只要有人搬出一条长凳子往路中间一放,挡路了,那就是邀请乐队来一段文艺表演。有唢呐演奏百鸟朝凤,鼓乐队敲什么大得胜。这小伙专门表演干板腔。大段子能说好半天。小段子张口就来。段子不长,但是两句一个转韵,干板腔说白就这样灵活——
有个人,和他娃,跑到地里看庄稼。杂粮五谷都长满,娃儿一看很稀罕。娃儿赶紧问他爸,怎么长下这庄稼。爸说土能生万物,种下什么长什么。只要种子土里埋,种下几天长出来。这个娃就不相信,打破砂锅往底问。我爷埋了好几年,怎么不露个人尖尖?他爸说,好娃哩,你不懂,你爷就不是正经种!
他拿手的段子,是民间传唱经久不衰的“憨女婿看丈母”的故事。这套民间故事,在晋南是一个系列,经常有人拿出来打趣。小伙子的段子,说的是憨女婿上门,丈母娘正在卧床,女婿撩起被子,把屁股当成了大脸盘。好奇怪——
没长眼睛没眉毛,两个脸蛋一道壕。我给*嘴里塞了一颗枣,光见囫囵不见咬。
这个当然说的是屁眼。巷道里顿时然会引起一阵哄笑。村干部觉得格调低下,脸上挂不住。可是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辛苦一年,找个空子乐呵一下,还管那么多干啥。不过说个笑话,讲什么崇高庸俗。村里一帮老百姓热闹,县里干部也懒得管那么多。
河津县的农民杨玉林,搜集编演干板腔多年,当地称他干板腔大王。他会一二百个段子。他的《打麻将》流传很广,村子里经常有人学演。讽刺村里老乡迷上打麻将上瘾,啥也不顾。
一说进了麻将场,天大的事情都忘光。进了场子一说坐,三天不吃也不饿。尿泡子憋得特了个特(大),小肚子险乎都撑破。宁受着,不离窝,哪怕尿下一裤裆。那么漂亮一个人,熬得满脸枯皱纹。人瘦了膘跌啦,脸蛋看上没血啦。不做活不买面,不管娃不做饭,不叠被不扫院,娘家妈来了顾不得回头看,扔给一个钥匙串,你先回去先洗涮,我的手气不敢断。
干板腔这种土戏,各地群众文化工作也很重视。作为一种喜闻乐见艺术形式,县乡的小作家就经常编一些段子,加上新鲜的时政内容,作为基层宣传工作的一种手段,由此也产生了一些好作品,有的还传播较广,影响较大。
比如我们县电影队王雨花编写的《春风吹暖一家家》,就是省市的获奖曲目。
庄稼比高齐刷刷,/果农富了一家家。/摇钱树,呼啦啦,/票子落下扑沓沓。/新打的深井水哗哗,/新铺的油路光踏踏。/新买“崩崩”密麻麻,/新开的汽车一挂挂。/粮食堆下一厦厦,/腰里票票一沓沓,/新房一溜蓝瓦瓦,/新装的家具一匝匝。/有线电视亮哗哗,/冰箱里放着哇哈哈。/床头上,安电话,身上装着大哥大。/摩托一踩哧拉拉,/抽烟全是带把把。/生活过得香呱呱,/全家老少乐嘎嘎。/生了一个小丫丫,/活泼健壮喊妈妈。/乐嘎嘎,笑哈哈,/狗撵鸭子叫呱呱。/改革带来好日子,/美得可该说啥啥。
在我的印象里,土戏就是老家乡亲们须臾不离的伴儿。出门懒洋洋地上工,他会来一句眉户剧叫板:走着!再模仿胡琴“尼古尼古将将”。老戏新戏里的台词,经常被他们活学活用指说眼前。穷得下一顿都成问题,他要唱眉户“抽一袋洋烟我把精神展咿呀外,高兴了小曲弹三弦也门黄——”家里屋漏墙塌,他要唱“骑白马,扛洋枪,里里外外三道岗,放个屁也蹦蹦地响”。有时候,他们也要抒发一下自己的职业自豪感,于是在犁地的时候,他们一甩鞭子唱,“手捉犁拐鞭打牛,老子不干你吃求”。今年棉花收购指标高了,他们也会发一下牢*,唱起“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公家要棉花呀,地里打不下呀”。村里很难见到一桌酒席,但他们一围坐最喜欢表演《奇袭白虎团》打翻了酒桌的段子,“美国顾问胡高参,急忙就往桌下钻,连汤带菜扣一脸,烫得嗷嗷乱叫唤”。他们说,这就叫穷乐呵,穷高兴。
前多年的乡亲们,愁吃的,愁穿的,经常为了几毛钱作难。可是人整天愁眉苦脸,还不要憋死。大约土戏,就是他们最好的伴儿。就说当下日子过好了,可是人生的路上,总有磕磕绊绊。总难过,总得过。唱几句土戏化解一下愁烦,暂时忘掉日子的重压,也是人生旅程的必要搭配。土戏就这样成了情绪的调节,生活的解压阀。由是在愁苦的年月,我也不时看到他们哼哼唱唱。土戏就在生活的夹缝里,顽强地生长。惊回首,已经成为民间文学的一项醒目的成果。

1980年代曾经有一个时期的老戏复兴,到世纪之初,戏曲辉煌不再,败像尽显。剧目衰减,行当不全。各家剧团首先裁撤丑角。生旦勉强撑门面,丑角扔到角落无人理睬。传统戏这样,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就更是这样。一群好人在哪里做戏,丑角没有戏份,演员越演越没劲。没了丑角行,传统的丑角没事干。运城的《苏三起解》获了大奖,女主角红透半边天,配戏的丑角离团失了业。现代戏表演更没有丑角的的戏份。当年那些蛤蟆功,顶灯功,歪嘴功,贯口念白,都成了过时的废弃物。
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喜剧,并不等于没有喜剧传统。中国传统戏曲强调表演的娱乐功能。丑角经常逸出剧情,独立进行念白表演。即便是悲剧之中的插科打诨,人们也习惯了欣赏过程中的情绪转换。乡下看戏,眼泪和笑声交替出现,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违背情理。现在,在山陕梆子的老窝,戏曲也竟然如此净化。一个格调不高,就把各种笑声排斥在外。大凡打趣逗笑,都属于庸俗无聊。低俗这顶帽子,吓跑了多少制造笑声的喜剧人,也让观众收敛了欣赏喜剧的意愿,觉得自己是不是低级趣味。舞台上没有了丑角的插科打诨,捣乱搞笑,所有的的噱头,都做为低俗无聊删除掉了。
山陕梆子本来自草根,架不住庙堂强势的移风易俗。
舞台干净多了,太干净了。与之相联系,太多的严肃庄正,太多的板正无奇。看戏,满目红光都是说教,娱乐不见了,趣味少多了。
怎么看起戏来,人都不会笑了呢?人都不知道笑了呢。
大家都在忙,生活中乐趣少多了。看戏,也成了一本正经。
日子过好了,台上台下的笑声反而不见了。
不禁怀念起土戏来。曾经匮乏的日子里,我们也不缺笑声啊。它是乡亲们的欢乐源泉,伴随着乡下人走过了穷日子。再艰苦的日子,再穷困的日子,也有开颜一笑的时候,甚至也有开怀大笑的时候。

作者简介:毕星星,山西临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原任山西文学副主编,作品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冰心散文优秀奖。他多年来致力散文创作,成绩斐然。散文、纪实文学多见于《散文》《中华散文》《随笔》等刊物,多次被《散文选刊》《青年文摘》等选载。主要作品:《大音绝唱》(长篇文化散文),作家出版社出版;《坚锐的往事》(散文随笔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走过带伤的岁月》,2013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出岁月的阴影》,2016年5月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山青石在》(许石青评传),2016年由中国联合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