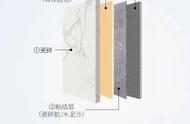清晨去市场买菜,转了一大圈,双手沉甸甸地嘞着疼,正要回家,忽然想起家中没有咸菜了,于是不情愿地折返菜市场,买了两个芥菜疙瘩。
芥菜疙瘩是我们这里最常见的咸菜,不用刻意的去酱菜铺子,任何一家菜摊都能买到。之所以总是忘记购买,是因为这种咸菜是过去家中腌菜的必备,让我下意识里把它归为不需购买之类。殊不知,家中已经很多年没有自己淹过咸菜了。
以前,每到临近冬日之时,父母便会买来多种菜类进行腌制。除了芥菜疙瘩以外,还有鬼子姜,地葫芦,白菜,胡萝卜,尖椒,韭菜,香菜,茄子……凡是市面上常见的、便宜的菜,大凡都会买一些来腌。
那时候,家里面最多的便是腌咸菜的容器了。大的有缸,小的有瓶,不大不小的是吃完酱豆腐空出来的罐子。在腌制咸菜的前几天,母亲会把她的那些宝贝瓶瓶罐罐全部拿出来洗一遍,然后整整齐齐地码在角落里阴干,阴干后再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晒一晒。用她的话讲:“来点太阳味儿。”
咸菜缸是不用洗的,因为它里面常年腌着芥菜疙瘩,随吃随捞。吃完旧的腌制新的疙瘩的时候,只需洗净那一个个长了胡须的大疙瘩,放进去即可,偶尔添点盐。据说腌制芥菜疙瘩讲究的便是这一缸老咸汤,咸汤不断,说明家里烟火不绝,是人丁兴旺的表现。老人们讲,在吃食匮乏的年代,这缸老咸汤不仅是腌咸菜的利器,也是人们吃莜面时候蘸的汤料,饱肚涨气力。缸里的咸汤要保持不坏,需要时常搅动,也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转换不同的放置地点,于是,咸菜汤的好坏,也成为了观察一家媳妇勤劳与否的标准。

我小时候,吃饱肚子不再是问题,人们已经开始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吃好了。所谓吃好,不过是餐桌上肉食的多寡。可到了冬天,甭管你是大富之家还是升斗小民,家中所吃菜的种类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白菜豆腐粉条和白菜豆腐粉条放点肉的区别。偶尔来个客人,能吃上一盘儿自制的西红柿酱炒鸡蛋,就算是上档次的菜了。
菜品稀少的原因无他,天寒地冻的坝上地区,没有新鲜蔬菜卖,即便有南来的大棚菜卖,也是逢年过节时才有,价格不菲且品种单一,我能记住的只有芹菜、蒜薹、葱头几样。这几样也是耐寒易储存的。
吃一冬天的白菜豆腐,清汤寡水的谁也受不了。为了调节寡淡,腌菜就成为了必需品,腌咸菜,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家家户户入冬前的固定步骤,谁也不敢在这上面偷懒。否则,冬天的嘴和肚子就要受苦了。
大规模腌咸菜的日子集中在芥菜疙瘩下市的那几日。淳朴的农民们一起赶着马车进城,车上是堆积如山的芥菜疙瘩。进城后四散开来,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走一个方向,沿街叫卖。其实也不用叫卖,人们早就等的望眼欲穿了。这就导致了“沿街叫卖”不用真的沿街,一般到了路口就被围住,可以预见的好买卖让农民们笑开了颜,也让一路费力拉车的马儿们可以歇一歇,低着头去吃草料袋里的草了。

买芥菜疙瘩很简单,问好价钱就行,不用挑,坏掉的早被农民们捡了出去了。人们根据自家人口算计好了买几袋,付了钱自己往家搬。卖方市场下的农民朋友们,也享受了一把供销社营业员的待遇:买菜的人都笑着脸,自己坐在马车边上叼着烟卷,拿着钱,看着这一个个城里人争先恐后地给自己递烟。
递烟的人一般是家远些的,他们希望过一会农民朋友能赶着马车给送上一趟。也有那心急的,自己推着自行车来,后座上、大梁上撂满了袋子,一步步艰难地朝家走去,没几步就大汗淋漓。也不知平时总被城里人看不起的农民们,会不会在心里暗自得意:哼,你们也有今天。
买来芥菜疙瘩后,就是全家人一起动手的时刻。女人们洗菜,男人们往缸里放,老人们撒盐,孩子们闹腾。一大缸咸菜用不了多久便会填满,最后上面放上一块磨得比少女的手还润滑的大石头,腌制便算完成了。剩下的过程,就交给了时间。
芥菜疙瘩属于大规模、普遍性的腌制,剩下的小规模腌制,就依据各家的口味了。我家常常腌制的,还有酱菜和泡菜。
酱菜是大杂烩。地葫芦、鬼子姜、尖椒、胡萝卜洗净后一股脑地放进酱菜罐子里,倒上酱油等调味品,封口即可。此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最难。因为稍有不慎,比如洗菜的水没沥干,酱菜就会坏掉。为了防止酱菜坏掉,腌制者必须是熟能生巧的老手,我家时母亲和奶奶来操作,父亲和爷爷只能在一旁唠叨:“酱油放少了,菜没压实……”当然,他们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去一边呆着去,大男人咋这么能唠叨?”其实也不怪他们唠叨,这酱菜,是他们冬天下酒的良伴。
我们这里泡菜的腌制分为两种,一种是圆白菜、芹菜和胡萝卜丁的腌制,一种是大白菜和萝卜缨子的腌制,统称酸菜。酸菜不用腌制太多,只要温度合适,几天便可食用,可以随腌随吃。毕竟,冬天有的是白菜。

腌咸菜也有小朋友的专属。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罐头瓶子,就是为我们准备的。这种腌制方法叫做暴腌。暴腌的咸菜品种很多,雪里蕻、白萝卜、韭菜、香菜是最常见的。雪里蕻是除了芥菜疙瘩以外腌制的第二大种类,之所以我没有写,是因为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当莜面蘸蘸,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它不熟咸菜,属于“正菜”。而罐头瓶子里腌制的雪里蕻,才是我的咸菜。它与缸里腌的区别是,妈妈和奶奶会在里面加少量的糖,吃起来有甜味。
不过,加糖的雪里蕻我能吃到的机会不多,大多数时候被父亲以孝顺爷爷的名义拿去下酒。我吃得最多的暴腌咸菜,是白萝卜。小瓶子腌制的白萝卜要加很多糖,其口味彻底变甜。甜口的咸菜父亲和爷爷都不爱吃,母亲和奶奶不舍得吃,于是,它们就成了我的专属。腌好以后,捞几根白萝卜条,咬下去凉凉的、脆脆的、甜甜的,就着米饭能多吃两碗。
至于腌韭菜和香菜,说是给小孩子的,其实也是父辈们的下酒菜。说起来,好像父辈们的待遇比孩子要好,几乎所有的咸菜腌制都是以“下酒”为标准,在选择腌制何种菜时,男人们的意见格外被尊重,也许,这是过去农村流传下来的习惯,毕竟男人们是劳力,一家之主。
入冬后,咸菜陆续腌制成功。每到吃饭时,桌子中间摆上一大盆子冒着热气的炖菜,在它的四周,是几盘或者多达十几盘的咸菜,绿的鲜嫩,白的透亮,红的喜庆。一家人围坐桌前,吃着炖菜,就着咸菜,构成了我童年最美好温暖的画面。

如今,老一辈儿的人相继离开,剩下的也到了懒得折腾的年纪,腌咸菜这项过去的冬日必备工作,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也正常,现在冬天蔬菜品类丰富,人们自然就降低了对咸菜的依赖,有时候家里腌点咸菜,也是吃不了倒掉的居多。更何况,菜市场里卖咸菜的商家那么多,口味那么全,每次少买一点就能吃上许久。真的不需要自己再去腌制。
可不知为什么,每次买来的咸菜吃到嘴里,总是少了一点味道,家的味道。少了家的味道的咸菜,就真成了咸菜,骗骗嘴,苦苦心,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
作品均为原创
请关注风舞鹰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