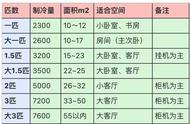我手写我心,我文传真情。
在浩瀚博大的故乡面前,我只是肥沃泥土里的一粒,在丰富多彩的故乡面前,我只是春生夏绿秋黄冬落的轻飘一叶。在徽味繁复美味传扬的故乡面前,我不去做巢湖三白,不去做黄鳝泥鳅,不去做千里飘香,不去做腊味合蒸,不去做美味芹芽。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吟诵道:“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是的,水草在柔波里可以自由飘逸,无拘无束。而我呢,出身微末,也没有起于青萍(时至垂老,依然为生计而谋),我最多只能做家乡的鸡毛菜—— 一种柔嫩,纤细,甚至都有营养不良征兆的小菜。
是的,我就是老家的鸡毛菜。我命贱,所以我适合任何地方生长,菜园子给我留一块地,专门用来让我生长,那是我的荣幸。我和番茄,黄瓜,豇豆,大椒子们一块地里生长,我诚惶诚恐,于是自觉不自觉就矮了几分,藏在他们中间好不显眼。被忘记有的时候反而生长得更加快乐。房前屋后只要有空地,我也不嫌弃,有的时候可能还有没有捡拾干净的小石子硌的腰疼,我也不抱怨,虽然细碎的土壤更适合我生长。有地方就不错了,这很符合我多年来我辗转奔波的命运,或许好一点的环境更适合我,但是我没有权力挑剔,是什么命就认什么命。
我的生长成本并不高,种子撒下去,浇点水,这是我存活的基本要件,有了这,我就可以奉献一些景色,贡献一点作用。
老家人每天早晨都要担着一夜积攒的屎尿,到自留地,给番茄黄瓜豇豆等上肥料,他们可以生产出更多价值,农人们也就格外精细的照料。番茄要用木棍支撑,黄瓜豇豆要搭架子。他们还需要修枝,打也,可能还需要农药。而我呢,没啥要求,也就是浇个水,最多杂草喜欢和我作伴,太旺盛了,咱拔掉。如果有多余的粪水,多加水,我也不嫌弃。有心细的,喜欢我的,也给我盖层薄膜,我感激涕零,用更好的生长来回报。
我永远长不大,或许是基因的原因,我不能像番茄红的诱人,不能像黄瓜翠绿的诱人,不能像豇豆修长的诱人。我最多只能长到食指那么高,我的叶上常有虫咬的痕迹。
番茄黄瓜豇豆被主人细心的摘下来,分成不同的类别,主人盘算好价钱,放进筐里,扁担挑着,吱呀吱呀的走进菜市场,去换取更好的价钱。它们论斤卖,主人用心推荐它们。
我被主人一堆摊开,放在一个角落,或者被扎成一把子一把子,码放在框外,我是论把子卖。
番茄有多种做法,它可以生吃,可以和鸡蛋炒(据说这是做饭的入门菜,犹如切土豆丝,蓑衣黄瓜是学厨师的开始),还可以和许多高档食材搭配,竟然还可以烧汤,且是全国各地喜爱的酸甜口。黄瓜凉拌,全国流行,可以凉拌成多种口味。还可以清炒,搭配多种食材炒。竟然可以做成腌菜,且老少咸宜,不失为夏日开胃的酸黄瓜很是流行。豇豆呢,成熟后豆米可以大有用途,青绿的时候最适合做老家的腌豇豆。稍微老点,就可以晒成干货,便于储藏。冬日里大荤配干豆角,干豆角饱吸荤汤,很是诱人。这也是全国流行的吃法,老家人也是精于此道。
而我呢,在我所知范围,我并没有什么全国流行,我只在老家受欢迎。然而我毕竟属于小众,毕竟没办法进去大雅之堂,我只有两种用途。
清炒。菜籽油烧热,浓烟四起,香气四溢,鸡毛菜往锅里一倒,浓烈的的油和柔弱的我接触,我瞬间沉醉,身体更加柔软,少许盐,几下出锅,虽然柔嫩,然而我不是筋骨相连,藕断丝连的那种,我虽小而清脆,我柔弱却果断。品我者,赞不绝口。我小小的身躯里竟然隐含着关于故乡的精神。
烧汤。我是清汤清淡,高汤清香。我身子弱,我不堪猛烈,清汤高汤烧开,各色食物下锅,所有的调味完成,只在出锅前,我加入团队,锅开即可。我不是主角,但我的翠绿可以起到点缀,甚至激发食欲的作用。初次接触我的人,只一口,就立即被我的清香清淡清脆吸引。在老家名扬四海的诸多大咖之后,接触过我的都把我当做巢湖最默默无闻的佳品,一如巢湖老家,绝不炫耀,始终低调一样。
老家鸡毛菜用揲的方式采摘,揲念作“di”,我太娇嫩,不适合采,也不适合摘。我只适合二三指轻轻地往上提。
这就是我文字里的鸡毛菜。这就是我文字里的故乡。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