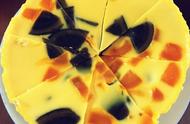作者:刘东黎(中国林业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土生万物,地载群伦。”土地是万物的根基,生命、生产、生计、生活、生态、生业等皆与土地有关。人在大地上培育作物,保护大地上的农作物和生态,在表面上是一种营生,是为了得到维持生命的那一点食物,但其实,是在另一种非凡的意义上进行筑造。劳作,就是人在故园的扎根方式、定居方式。寒来暑往里劳动、耕耘与收获,能帮助人们坚定信仰,通往永恒。
万物自行绽放
世界有时可以从一副简单的农具、一株普通的植物、一件沉默的艺术品中涌现。大地是承受者、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为岩石和水流,涌现为植物和动物。
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

农鞋(油画)凡·高
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凡·高名画《农鞋》的解读,传递出一种拨动心弦却又难以言说的思绪。暮色黄昏,画面中未出现的农妇脱下鞋子;晨曦初露,农妇又把手伸向它们;或者在节日里,农妇把它们弃于一旁。劳作者的眼里没有风景,这一切对农妇来说实在太过寻常了。然而在无声的召唤与模糊的直觉里,一双布满风霜的农鞋,在作品中走进了存在的光亮。
通过一个器具,农妇被置入存在者显现的恒定中,被置入大地无声的召唤里;农妇自此才对自己置身的世界有了把握,世界和大地开始为她而在。
在海德格尔眼中,农人的劳作与自己的哲学思考非常类似。他本人的工作室就设在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斜坡上,只有三个房间:厨房、卧室和书房。从窗口望出去,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茂密的杉树林。墨绿色的丛林中,不时闪出一片淡绿色的林中空地,在阳光下,白羊黄牛、红瓦灰墙一一可见。天天往返于田间小径,穿梭于林中路上,海德格尔思考着“不可替代的大地根基”:
那永不停息的涌动者,荫蔽万物,让万物如其本然地显相,让万物自行绽放,聚集万物而让其持留者,到底所为何来?
答案就在大地的风景和艺术中。一双农鞋,连接着生命的来路与去路。凡·高的画让我们看到了一双农鞋的“存在”,也让海德格尔看到,农业与哲学有着最直接和最简单的联系。因为,农业是生发和维持人生存意义的源头。人之为人者,是他能在身处劳碌耕作的境遇中,根基留在地上,仰望直抵天空,由此加入天地人神的合舞。这也保证了仰望最终得以贯通天空与大地之间。这一“之间”则分配给人,构成人的栖居之所。四者安排得如此美妙,仿若生命的起承转合。
烟云横流的循环之舞
在另一首中国古诗中,我们看到了与农鞋类似的器具(农具):
利器从来不独工,
镰为农具古今同。
芟馀禾稼连云远,
除去荒芜捲地空。
低控一钩长似月,
轻挥尺刃捷如风。
因时*物皆天道,
不尔何收岁杪功。
元代王祯的诗歌《镰》清晰表达了先祖对农具的深邃认知,是一种“大地诗学”的范例。一把镰刀,一种再寻常不过的农具,同样参与了天地人神相互应和的“循环之舞”。诗人出其不意地用了云、月、风等事物与之比拟,甚至关联着高不可问的“天道”。
“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柳宗元《首春逢耕者》)在永州郊外,柳宗元在春耕时无限眷恋地抚摸着农夫的犁耙,回看漫天霞光,对天意流转的敬畏化作静穆的宁静。这首诗不应解读为贬谪路上天色欲晚、人生将残的怅然。烟云横流在天地人神的“循环之舞”中,四者相互映衬,相互隶属,相互响应,相互照耀。
“烟暖土膏民气动,一犁新雨破春耕。”(释智愚《颂古一百首》)世界与大地不可思议的雄浑张力,就这样深刻地聚集在被诗人凝视的镰刀、抚摸的“耒耜”上。人培育和保护大地上的农作物和一切生长物,在表面上是一种营生,是为了得到维持生命的那一点食物,但其实,是在另一种非凡的意义上进行筑造。如果一种劳累与功绩,只为追逐和赢获最终的作物,那它们甚至是在反对和禁阻着生存的本质。农人对生长之物的培育,建筑师对艺术作品的建造,匠人对农具的制造,在最深刻的意义上,都是在用神性,用天地人神的“循环之舞”来度量人身。
土生万物,地载群伦
世界上本来没有“农作物”这种东西,它们都是从野生植物(主要是草本植物)驯化而来的。从“草”到“禾”的转变,意味着某种形同进化般的重大改变。种植作物需要对田地进行分配,农业时代的饮食起居、筑场修屋等等,无不与作物的照料或看管有关。家人与邻人在田地中进行劳作的场景,使古人对于“边界”“产权”有了最初的意识。

耕织图(之一)(中国画)资料图片
最重要的是,照料作物需要一个稳定的居所。当“植株的固定”引导了“人类居所的固定”,就得结束游牧状态,和自己的“作物”一样定下心来,扎根于大地的某一位置,狩猎采集从此成为副业。不断迁徙的状态越来越令人厌倦,人类开始有了“家宅”或“屋宇”,“诗意地栖居”也就成为可能。
“粮食”是沉重的,相对而言,“蔬菜”是轻盈的。“蔬菜”总是存在于亲和性、家常性的空间,如菜园里。它远没有“庄稼地”那样富有文学意味,因此不太容易被引领朝向艺术的升华。不过,蔬菜也有着精神性的艺术形象,比如商朝遗民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采蕨”,故事流传至今。“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农作物保存着某一时代中人类生活与植物之间关联的原初经验,而且“人不会真正的从水、燃料、蔬菜中异化。那些都是古老人类之根”(斯奈德语)。
阳气在田,万物生焉
古老的山毛榉和黑色橡树挺立在平原上,成群的牛羊如繁星点点游走于它们之中,还有一点忧愁的气息,弥散在光彩迷人的景色之中。这是维吉尔《牧歌》里的乡村景色,是田园文学的真正源头。维吉尔的《农事诗》四卷,则以教诲为基本内容,穿插着神话传说和对意大利农村风光、农民生活、日常劳动的赞颂。第1卷主要讲谷物种植,第2卷讲葡萄和橄榄,第3卷讲畜牧,第4卷讲养蜂,几乎是文学式的科普写作。自然代替了神职人员,通过农事诗的清唱,人与神合一,将人类提升到新的美德高度。
“农事诗”,一般是指“描述农事以及与农事有关的政治、宗教活动及日常生活的诗歌”。人之栖居在本质上是诗性的,这种诗性不是栖居的装饰品和附加物,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土地育化与繁衍的能力,是最具有传说乃至神话意味的人类原始生活场景。

维吉尔《农事诗》英文版插图
作物从土地中生长出来,土地一定具有孕育生命的潜能。在赫西俄德叙述世界开端和最早一代希腊神祇产生的《神谱》中,宙斯的姐姐德墨忒尔是丰收和农业女神,她在古希腊雕塑中的造型是“一位从地表中探出上半身的卷发女子,双手上举,手中握着结穗的谷物”。由于农业是广大农民定居和安乐的基础,后来德墨忒尔又成了立法、家庭和婚姻的保护神。
在东方,则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经·乾卦》)之说。可见“文明”一词最初的记载,就与农耕有关。经学家孔颖达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是故古代的帝王行“耤田”礼、率众亲躬的仪式,竟然从周代延续到清末,无他,盖因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元代《农桑辑要》序)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诗经·小雅·甫田》)先民于万物复苏的春季,祈盼五谷丰登,谓之“春祈”。秋日收获,仍须祭献于土地,谓之“秋报”。春秋流转的土地上聚集着神性,因而被赋予了万物的根基与源头之意。
土地不仅是山川河流的护持者,更是邦国的象征。“(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块”象征土地,是最要紧的“命根”,生命、生产、生计、生活、生态、生业之六生皆与土地有涉。天人感应,时空一体,人世兴衰旁通于土地与作物,正是人间宏阔运行的自然之道,亦筑成上古华夏国家的根基。
“农事”一词在《诗经》中并未出现过,不过朱熹曾在《诗集传》中给出了《诗经》中11篇与“农事”相关的具体诗作篇目。不着意雕琢的歌咏,天真纯朴的吟唱,劳动者种田、养蚕、纺织、染缯、酿酒、打猎、修筑等劳动场景,定格于千年岁月,无不是在世伦理的核心关怀。
“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论贵粟疏》)。古代汉语的“社稷”一词,是汉语文化永恒的母体和原型,它保留着“农业”与“国家”的原初关联痕迹:“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前者是对“大地之神”庇护之力的崇拜(社祭的神坛也称为“社”),后者则是对“作物之神”生养之力的崇拜。“社”代表安全的生存空间,“稷”代表稳定的食物来源。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粒米,能盛尽天下悲苦,有如“一个民族的秘史”。农业是人间最苦的职业,农民是天下最苦的人。大地的富足和宁静,需要农民以一生劳瘁、满身伤痕为代价。崔道融《田上》诗曰:“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这是诗人于雨夜之中,看到冒雨耕作的农夫,叹息良久,有感而发。“尽日扶犁叟,往来江树前”(李白《对雨》),也是在说农人终日劳苦耕种,即使在阴雨天也不能休息。民生之苦,稼穑之难,呼唤着诗人的悲悯与良知;客居异国他乡的游子会把生育了他们的“老娘土”带至天涯海角,也是对土地浃髓沦肤的无上感戴。
不违农时
中国现存最早历法文献《夏小正》,详载了一年十二个月与不同月份的物候现象。农作物生长、成熟的状态在不同的节令下表现不同,就连与之相关的动物,也有蛰眠、苏醒、始鸣、交配、繁育、换毛、迁徙等物候现象。先民生活在自然之中,对季节性的物候转折远比后人敏感,对自然的感知和情谊也就更加敏锐和深厚。照料作物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们去认识时间轮转、四季更迭、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决定和制约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也正因如此,农耕社会的生活是从容的,有节奏的,生活的节奏与自然同频。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概以时令为转移。春节、立春、清明、夏至、重阳、冬至等,都是与农时有关的时间节奏(以及与亲人相聚之时)。与历史积淀同样厚重的欧洲相比,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没有阴影,没有古风,没有秘传,没有绚丽而又昏默的冤孽”,而单纯是天地人神的流转相遇,是非对象化、氤氲涵浑的节日、佳(家)节。
《尚书·尧典》记载舜帝的话“食哉!唯时”,记尧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庄子·德充符》中借孔子的话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作物的生长随气温变化,生根、发芽、抽枝、展叶、开花、结果,“人时”同样也要符合自然法则,读书入仕者也要将四季农时了然于心。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自然的天象与节气是天、地、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与节奏,是万物与人生的和谐之处,本就含有不寻常的交汇与经验的构成。“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白居易《观刈麦》)看似细微琐屑的事物,却在微小中包含了家族情感、民风习俗、人际交往等,蕴含着素朴的真理。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经·周颂·丰年》)对于华夏民族而言,国家的政治甚至都带有农业物候特征,是为“节候政治”。一定的季节,就行一定的政令。四时郊祭礼仪与农业生产对季节的要求浑然一体,神圣的顺序不可更改。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礼记·月令》)四时物候决定着植物、动物的生长,也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基本形态。比如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之气相混合,于是草木萌芽。天子会亲自颁布与农事相关的法令,农官依旨前往东郊,修理冬天荒废下来的耕地疆界,把沟渠路径重新查明修理,根据不同的地形特征,种植不同的作物。把握农作物生长时间、观测动植物生长活动规律的生活技艺,与对自我生命规律的认知高度重合。农事与节气,就是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时间。
农事如同诗歌、歌谣、节日一样,有格调,有节奏,有智慧。《诗经》中相当数量的农事劳动描写,开启了东方农事写作的源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反映了一年四季多层次的工作面和高强度的劳动,是“农事诗”的起源和典范。如崔述云:“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气候的变迁带来劳动方式与景物的变迁,昼之阴晴与夜之浊清交替更迭,深度影响着人的思绪、情感、气质、性情以及审美态度,最终影响到文学艺术的风格面貌、文辞舞咏。
诗就在农田的近旁
“生”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颇似草木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形态。单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农作物不是奇花异草,缺少构成“风景”绘画、山水诗作等所必要的透视法、事物轮廓和相关的艺术理论。
然而,“就在粮食的近旁产生了诗”(普里什文语)。阳光、草木、原野、禽鸟,以及与此相连的原初语境:物候、星象、季节、劳作、繁衍……大自然的壮丽语境,尤其乡土生活中存在与保留的自然之象,比如麦子、河流、庄稼等,无不是艺术世界最基本的母题。
“双手劳动,慰藉心灵”(海子《重建家园》)。海子的诗带有一种“原诗”的性质,纯粹、明朗而神秘。麦地就是诗人理想中的人神和谐共处的家园,是心灵能够栖息的精神实体。农夫粗糙的身躯沉没在田野里,笨重的膝盖深陷在泥土中,艰辛的生存与劳作,使得农业、土地与作物同时具有一种沉默、痛苦而又耀眼燃烧的诗歌意志,对于包括工业文明在内各个时代的思想艺术,都具有无可回避的、隐秘性的塑造作用。它带有一种直抵本质的生存哲学与诗意,穿透束缚在人身上的意识形态、道德情感、价值观念,持久影响着人类的终极关怀。
“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土地令他们拥有了家庭,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土地成了他们的上帝。土地中有财富与秘密,土地在他们的锄头下翻转……或许土地本身就是一种轮回。他们在土地上耕作,一起劳动,一起在土地上创造成果——无需任何言语。”(赛珍珠《大地》)人世沧桑,唯有土地依旧。古老文明在历史的动荡中迟缓前行,犁铧沉重,但土地是他们此生的起源和终结点;土地的生息枯荣和庄稼的新陈更替,构成了他们人生的全部。他们身上的蓝袄,田垄里的绿苗、土黄色的干涸河床,共同构成乡土中国沉默而永恒的风景。土地诞生一切,养育一切又收纳一切,这是农耕民族共同的生命背景,最终凝成了壮丽的大地诗学语境,成为折射我们生命情感的荣耀之光。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失望和希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穆旦《赞美》)。土地是万物的负载者,兴盛与衰亡的命脉都根系于土地之上。田畴墓地间承载了人类生活的轨迹,托举起古老凝固的文明,以及所有的人事繁衍。农民是历史的支撑者、沉默者,他们安土重迁,安于永远轮回的生命,乡村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是古老族谱里无尽循环的历史,书写着一方血脉的绵延连亘。人栖居之处即为家园,离开它时,则成故乡。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庄,/岁月尽竭了,牲口憩息了,村外的小河冻结了,/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穆旦《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略显荒芜的村庄里,虽然是北风凄紧,寒意彻骨,但也能看到、忆起并感怀农村生活的灵魂和气息。诗人目光里全是与农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一种感性氛围悄然化解着寒夜,成为一种慰藉的力量。那些被岁月销蚀的事物,散发着悠远陈旧的气息,锄头、牛轭、石磨,是承载无穷回忆与希望的容器。这些事物也许仅为自己而存在,然而在宽厚的大地上,诗人倾听村庄的声音,真正领会到家园的存在。
“无边无际的大玉米地里有什么?肥壮的玉米棵遮天蔽,一片连着一片。无数的刺猬、兔子、黄狼、草獾,还有狐狸,都从里面跑出来。各种鸟雀一群群钻进钻出,喧闹着。你站在玉米地边,可以听见十分古怪的声音,有咳,有笑,有呼呼的喘息”;人在玉米地里,好像“来到真正的家,身心都放松下来。玉米缀的气味,泥土的气味,青草的气味,什么都混到了一起,涌进肺里。这气味养人哩。”(张炜《钻玉米地》)这也是在诗意观照下的自然村社,隐藏在大地风景之中,和世界发生着神秘的关联。玉米地里透着大自然的繁茂气息,让人们可以在一种更加亲密、友善的关系中彼此相处。粮田和作物,化作人类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同时让农人在大地上找到他们的归属感。耕耘栽种、滋生繁育的奇迹,生命一次次轮回转化,开启生生不息之源。这是传承千年的土地哲学,也是亘古不变的生命至理。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作为大地生命共同体中的蚂蚁、蜜蜂、麻雀、杜鹃、野兔、驴子、麦子、麦田、树林等,在很多时候,很难成为被欣赏的对象。人们寻常不会有像苇岸那样的领悟:“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对大多数人来说,田野与土地只意味着艰苦的劳作。乡村会有静谧、纯真、简单、富足的时刻,然而,它毕竟与辛苦相连,与年复一年的重复相连,却难以与诗意或审美相连。
但诗歌确乎在农田与野地之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用过书桌,我也从来没有用于写作的房间”——诗人弗罗斯特长期生活在乡下农场,他的诗就是在农事间隙,倚靠着树桩小憩时构思出来的。对他而言,自己的生命就像是一种依附于大地的植物。和所有的农夫一样,诗人生活的世界,完全依托于田垄、泥土以大地慷慨的馈赠。
1935年,利奥波德举家搬至威斯康星州沙郡北部的一座破败农场,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拥有一片土地,靠自己的努力去研习大地之上的动物、植物”。他发现鸟儿不仅是自然界专业的歌手,还是最优雅的舞者;枯橡树居然还能为松鸡提供庇护;而蓝翅黄森莺已经在农场安心地筑巢安家了,这是何等的信任啊。“风很忙,忙着在十一月的玉米地里奏乐。玉米茎哼唱着,松散的玉米棒半开玩笑地弯曲盘旋着向天空轻轻挥动,风则忙碌着继续前行。”
清代郑燮“毕生之愿,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花草,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俱见烟水平桥”;可见这种回归田园的心愿,古今中西攸同。这里无所谓仕与隐,也无所谓城市与乡村,人与粮食、土地与村庄,一切自然而然,呈现出最本真的生存状态。
与此同时,人在大地上培育作物,保护在他周围生长的东西。对地方、植物、土壤、气候循环和生物群落的深入认知,既古老也现代,是人类知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劳作,就是人在故园的扎根方式、定居方式。
寒来暑往里劳作的耕耘与收获,能帮助人们坚定信仰。扎根,就是克服“飘荡”“失衡”,它通向永恒之途,复归存在之根。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9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