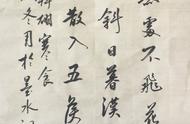罐肠竟使这位同学如此的深情怀念,难怪在外的祁县人返回所在时都不吝携带。
罐肠是家乡祁县用荞麦面做成的的一种美食,寻常巷陌都可见到。好多人写成“灌肠”,其实我以为是“罐肠”,因为老以前的时候,它是用勺子灌倒一个有深度的小罐罐里的,然后放到蒸笼里蒸熟。

祁县人爱吃灌肠,六七十年代,家境贫寒,吃不起肉食,罐肠也就成了人们解馋的美食。花五分钱买上一小罐,拌上蒜泥,倒上醋水,滴点香油,吃了还想吃。我特别爱看打罐肠的打罐肠。从木箱里拿出灰青灰青的一小坨,拿在手里,右手就用解手手(一种切罐肠的小刀)开切。左手不动,右手在罐肠上一拨一拨的快速旋转,有的一边转一边点头,有的还有节奏的踮脚,特有意思。几秒钟的功夫,短细短细的、带弧形的罐肠就打好了,好像一条条软软的青色小鱼。往你碗里一放,再给另外一个瓶子,摇一摇,倒点蒜泥做成的水,然后把你的钢镚儿往袋子里一装,便又扯起嗓子喊:“打——罐——肠(祁县人读za)——了。”那吆喝声不知要拖多长,还绕着弯子,在空中盘旋,一直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今一看到罐肠,便想起家乡的那个买罐肠的大爷,那声音至今还响在耳旁,勾起你无穷的遐想。

祁县的罐肠不靠什么色素招徕人的眼球,永远是灰青灰青的面的本色;也不靠什么怪味来刺激人的胃口,用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盐,佐以蒜泥、醋和香油,这样便成了人人爱吃的美味。我想家乡罐肠的原始制作者一定深谙“五味令人口爽”哲学道理,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你了解一下罐肠的制作过程,你还会深深感到,祁县人是靠工夫和智慧把荞麦面的灵魂给激发出来的,然后才有了我们看到的灰青青的可人的罐肠小面坨。祁县有个做罐肠世家记载了这个过程:

做灌肠是个力气活,灌肠的魂在于面,纯纯的荞麦面和颇费功夫的和面过程。和面是个大工程、力气活,直径一米的大缸,荞麦面、盐按比例混合,一斤面一钱盐、四斤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比例,诀窍在于加水的速度和量,先是把面和成絮状,再揉成团,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加水,再把面团一点一点稀释,稀释到能把面提起来的程度,开始摔打,用手捧起面一遍一遍的甩在缸里,直到把面的筋骨摔出来,那个费劲程度至少相当于一个成年男人跑个五千米,摔好的面,再一点一点往进加水,一点一点的搅匀,如此反复,直到把量好的水全部搅进去为止,这时候的面就像我们摊煎饼的面糊,用勺子舀起来既不能挂勺太多也不能不挂。
和好的面舀在碟子里,准备上笼蒸,如果说和面是技术活,舀面就是技巧活,舀面的时候一手端盆,一手拿勺,分分钟的时间填满一个笼屉百十个碟子,舀面的而过程基本做到了不流不溢不滴,盛在碟子里的面糊不多不少,多了成型的灌肠太厚,少了又不成型,八到十分钟灌肠出锅,烫手的的灌肠碟五分钟内从笼屉取出一排排立在干净的地上,腾出的笼屉准备下一轮上锅,这个过程恰恰是蒸灌肠的八到十分钟。
这使我想起了名贵中药的制作“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原则。我不知道当我们用筷子夹起软软的罐肠愉快的品尝的时候,是否也品尝到了它里面凝含的艰辛与智慧。可以说,任何真正的美味都经过了人力和智力的“千锤万凿”和“千淘万漉”,才可能素颜出场,惊艳世人。